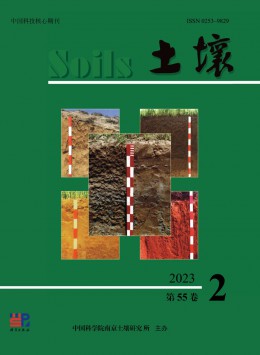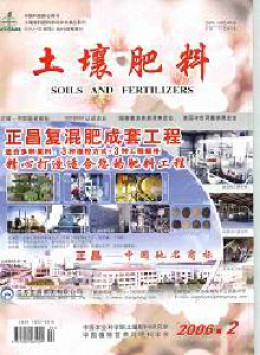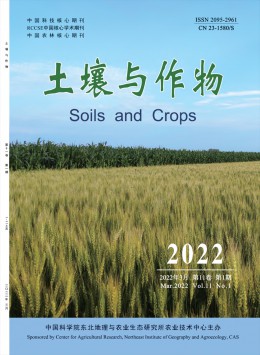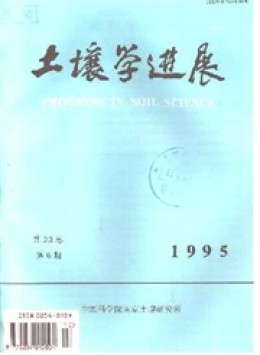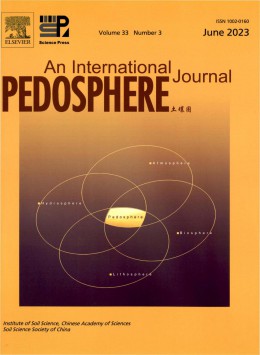土壤環境特征精選(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誕生,需要你不斷地搜集資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編為你收集了豐富的土壤環境特征主題范文,僅供參考,歡迎閱讀并收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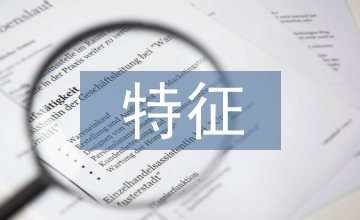
第1篇:土壤環境特征范文
(臺州學院 生命科學學院,浙江 臺州 318000)
摘 要:本文以浙江省臺州市路橋區峰江地區電子廢物拆解回收場地為對象,主要考察了電子廢物拆解地土壤中重金屬污染的分布特征.結果表明,在考察的5種(Cu、Zn、Pb、Cr、Cd)重金屬中,除了Cr和Zn外均在一定程度上超過《國家土壤環境質量標準》二類土壤環境質量標準,污染最嚴重的是Cu、Cd,其次為Pb.以國家土壤環境質量二級標準計算該典型區Cu、Zn、Pb、Cr、Cd的綜合污染指數為4.3,已達嚴重污染程度.表明該電子廢物回收跡地土壤存在嚴重的重金屬復合污染問題,已不適合農業耕作.
關鍵詞 :電子廢物;重金屬污染;土壤;分布特征
中圖分類號:X70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260X(2015)01-0140-03
1 前言
電子廢物,又稱電子垃圾,是指各類報廢的電子產品,包括各種廢舊電腦、通信設備、電視機、電冰箱以及被淘汰的精密電子儀器儀表等[1,2].20世紀以來,隨著電子信息等高科技產業迅猛發展,電子技術的更新不斷加快,全球越來越多的廢舊電子和電器設備被淘汰.在許多發達國家,電子廢物已成為增長最快的垃圾流[2,7,9,10].世界上約80%的電子廢物被轉運到亞洲,其中有90%以“回收”等名義輸入到中國[11].
電子廢物中含有大量的銅、鎳、鉛、鎘等重金屬,電子廢物的拆解回收可以帶來廉價的原材料和豐厚的利潤[3,4].但是電子廢物不合適的處理方式,同時也導致有害重金屬進入環境,對人類的身體健康和生存環境造成嚴重的危害[5-8].浙江臺州地區是中國最大的電子廢物拆解回收處理中心之一.當地居民采用電線電纜的露天焚燒、電路板的烤制熔化酸洗等原始粗放的方式進行電子廢物的拆解,嚴重污染了當地生態環境[4,5].
在電子廢物回收活動對環境和人類造成的巨大環境危害引起國際關注的情況下,國內環保部門嚴令禁止電子垃圾的公開焚燒和隨意傾倒,但在暴利的驅使下,收效甚微[5,6,12].雖然路橋地區環保部門對當地電子廢物拆解回收進行了集中的整治與規劃,將所有電子廢物拆解回收作坊集中在同一條街道進行,但是由于拆解方式相對比較落后,拆解活動所帶來的環境污染問題還在繼續.因此,本研究選擇浙江省臺州路橋地區典型電子廢物不當處置地區峰江開展研究工作,通過對該地區電子廢物回收跡地土壤中重金屬的含量水平、分布特征的研究,對該地區電子廢物回收活動帶來的重金屬污染進行了初步的評價.
1 材料與方法
1.1 土壤樣采集
選取峰江地區某一拆解時間為20多年的電子廢物拆解地.其拆卸的電子廢物主要成分為家用電器的外殼、電板以及廢舊的電線等.采樣時,以電子廢物拆解地為中心,在離電子廢物拆解點邊緣0m、100m、200m、300m處分別采集3個平行樣.梅花狀采樣,分別取約1kg土壤(取距離地表2cm以下的混合土樣),將所取土壤均勻混合,土壤樣品經自然風干后,用瑪瑙棒研壓,通過200目尼龍篩,混勻后備用.
1.2 樣品的處理
稱取備用的土壤樣品0.5000±0.0005g,置于大玻璃管中,采用硝酸-高氯酸-氫氟酸全量消解法處理土壤樣品[13].采用ICP-OES測定土壤處理液中Cu、Cd、Zn、Pb、Cr的含量.實驗所用試劑均為分析純,所用水均為去離子水.并采用國家標準物質土壤標準參考樣GSS24、GSS25參比進行分析質量控制,分析誤差均在允許范圍內,并設置空白樣品同步分析.
2 結果與分析
2.1 電子垃圾拆解點土壤性質
本文對路橋電子產品拆解地周邊土壤的pH、總有機碳TOC(mg/g)、總氮(mg/g)、總磷(μg/g)及銨態氮(μg/g)含量做了測試分析,結果如表1所示.該地區土壤pH、總有機碳、總氮、銨態氮及總磷無顯著差異,表明各個采樣點土壤基本物理化學性質無顯著差異.與全國第二次土壤普查中該地區水稻土養分含量平均值(有機碳:24.5g/kg;總氮:2.45g/kg;總磷:0.41g/kg)相比,土壤養分含量均有所增加,而該地區土壤的pH則略低于該區全國土壤第二次普查結果(pH為6.0).可見,研究區電子廢物拆解活動并未降低其周邊農田土壤的肥力質量,卻降低了土壤的pH值,使得該地區土壤有一定的酸化.這可能與周邊電子廢物拆解的重金屬回收工藝流程有關.該工藝是將含貴金屬的廢舊電子產品以濃酸處理,取得貴金屬的剝離沉淀物,再分別將其還原成金、銀、鈀等金屬產品.而在該典型區,多半企業采用傳統的手工作坊式生產,很少集中處理剩余的大量殘留酸液,而是直接排于周邊溝渠、農田等場地,大量酸性廢水的灌溉破壞了土壤的緩沖能力從而造成土壤的酸化[10].而土壤酸化一方面會破壞土壤結構,使得土壤板結,抗逆能力下降,另一方面更為重要的是土壤酸化有利于土壤中重金屬向水溶態、交換態的轉化[7-9],增加重金屬在生物環境介質的移動性及其污染風險,從而降低土壤的環境功能,因此,該地區農田土壤環境問題應該引起我們高度重視[10].
2.2 電子廢物拆解地周邊重金屬的分布特征
表2為該電子廢物回收跡地土壤中重金屬的含量.該地區表層土壤Cu、Cd、Pb、Zn、Cr的全量均明顯高于浙江省該地區土壤背景值(Cu:19.77mg kg-1,Cd:0.20mg kg-1,Pb:24.49mg kg-1,Zn:84.84mg kg-1,Cr:58.51mg kg-1)[13,14].由表1可見,該地區土壤中Cu和Cd的污染最為嚴重,Cu的最大濃度為519.3mg/kg,最小濃度為249.0mg/kg,最大濃度為《土壤環境質量標準》(GB 15618-2008)中農業用地二級標準50mg/kg的10.4倍,最低濃度為《土壤環境質量標準》(GB 15618-2008)中農業土地二級標準的5.0倍.其次,該地區土壤中Cd最大濃度和最小濃度分別為4.5mg/kg和0.8mg/kg,為《土壤環境質量標準》(GB 15618-2008)中農用土地二級標準0.3mg/kg的9.0倍和2.7倍.調查還發現Pb的最大濃度達到56.9mg/kg,這個值已經超過《土壤環境質量標準》(GB 15618-2008)中水田、旱地、菜地的二級標準,表明不適合耕種,尚可作為果園用地.Cr和Zn的含量較低,沒有超過《土壤環境質量標準》(GB 15618-2008)中農業用地標準,主要是該拆解場地中幾乎不含或含有少量含Cr、Zn較多的電子垃圾, 如磁帶、錄像帶等.
由表1,各采樣點處Cu和Cd的含量均超出《土壤環境質量標準》(GB 15618-2008)中的二級標準,而Pb則是在回收跡地中心超出《土壤環境質量標準》(GB 15618-2008)中水田、旱地、菜地的二級標準,這說明電子產品回收活動隊對周圍土壤污染比較嚴重.在電子產品回收基地周圍300m范圍的土壤中,Cd、Cr、Cu、Pb、Zn含量隨距離增加快速降低.以國家土壤環境質量二級標準計算該典型區Cu、Zn、Pb、Cr、Cd的綜合污染指數為4.3,已達嚴重污染程度,表明該電子廢物回收跡地土壤存在嚴重的重金屬復合污染問題,已不適合農業耕作.
徐莉等[10]調查了浙江東部廢舊電子產品拆解場地周邊農田土壤重金屬污染特,發現檢測土壤中存在Cu、Cd總量超過土壤環境質量二級標準,Cu和Pd的濃度范圍與本研究相當,而Cd的濃度則是本研究的2~3倍,而相應地區土壤酸化很明顯(3.8~4.4),可能是導致Cd濃度較高的原因.潘紅梅等[11]于2006年考查了同一地區重金屬污染的狀況,發現Cu含量為435.67mg/kg,與本研究的結果比較接近.羅勇等[13]考察了廣東省龍塘鎮和石角鎮的電子廢物堆場附近農田土壤重金屬含量,發現Cu的超標率為63.7%,Pd的超標率為48.5%,Cd的超標率為78.8%,這與研究的結果也比較相近,可能是這兩地與本研究地所回收的電子廢物的種類和回收工藝比較接近.鄭茂坤等[12]考察了同一地區廢舊電子產品拆解區農田土壤重金屬污染特征及空間分布規律,發現Cu、Zn、Pb、Cd含量分別為Cu 118 mg kg-1、Pb 47.9 mg kg-1、Zn 169.0 mg kg-1、Cd 1.21 mg kg-1,其中Cu的含量為本調查結果的1/2~1/5,明顯較小,Cd的含量也較本研究低,可能是由于Cu、Cd的富集速度比較快,經過近兩年電子廢物的拆解回收,Cu、Cd的含量明顯增加了.
3 結論和討論
電子廢物回收活動,由于回收方式的粗放化,導致重金屬在周圍環境中不斷積累.電子產品回收跡地土壤中Cd、Cr、Cu、Pb、Zn中,除了Cr和Zn外均超過《國家土壤環境質量標準》二類土壤環境質量標準,污染最嚴重的是Cu、Cd,其次為Pb.以國家土壤環境質量二級標準計算該典型區Cu、Zn、Pb、Cr、Cd的綜合污染指數為4.3,已達嚴重污染程度.表明該電子廢物回收跡地土壤存在嚴重的重金屬復合污染問題,已不適合農業耕作.
——————————
參考文獻:
〔1〕Ha N N, Agusa T, Ramu K, et al. Contamination by trace elements at e-waste recycling sites in Bangalore, India[J]. Chemosphere,2009,76:9-15.
〔2〕UNEP. 2005. E-waste, the hidden side of IT equipment’s manufacturing and use: Early warning on emerging environmental threats no. 5, 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2005.
〔3〕王家嘉.廢舊電子產品拆解對農田土壤復合污染特征及其調控修復研究[D].貴陽:貴州大學, 2008.
〔4〕吳南翔,楊寅娟,俞蘇霞,等.舊電器拆解業對職業人群及普通居民的健康影響[J].環境與健康雜志,2001,18(2):97-99.
〔5〕Xing G H, Wu S C, Wong M H. Dietary exposure to PCBs based on food consumption survey and food basket analysis at Taizhou, China–The World’s major site for recycling transformers. Chemosphere, 2010,81:1239-1244.
〔6〕魯如坤.土壤農業化學分析法[M].北京:農業科技出版社,1999.235-285.
〔7〕杜彩艷,祖艷群,李元.pH和有機質對土壤中鎘和鋅生物有效性影響研究[J].云南農業大學學報,2005,20(4):539-543.
〔8〕Harter R D. Effect of soil pH on adsorp tion of lead, copper, zinc and nickel. Soil science Society of America Journal,1983,47:47-51.
〔9〕Clemente R, WalkerD J, Roig A, et al. Heavy metal bioavailability in a soil affected by mineral sulphides contamination following the mine sp illage atAznalcóllar(Spain).Biodegradation,2003,14(3):199-205.
〔10〕徐莉,駱永明,滕應,卜元卿,張雪蓮,王家嘉,李振高,劉五星.長江三角洲地區土壤環境質量與修復研究Ⅳ.廢舊電子產品拆解場地周邊農田土壤酸化和重金屬污染特征[J].土壤學報,2009,46(5):833-839.
〔11〕潘虹梅,李鳳全,葉瑋,王俊荊.電子廢棄物拆解業對周邊土壤環境的影響——以臺州路橋下谷岙村為例[J].浙江師范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2007,30(1):103-108.
第2篇:土壤環境特征范文
關鍵詞:土壤污染;生態環境;治理對策
一、土壤污染的現狀
隨著經濟和社會的快速發展,我國的土壤環境破環嚴重,土壤污染持續惡化。目前,全國土壤污染的超標率已經達到了16.1%,污染點的比例依次為重度污染1.1%;中度污染1.5%;輕度污染2.3%;中輕微污染11.2%,主要體現在工礦業、農業等人類生產和生活方面。我國的土壤污染類型主要表現為無機型、有機型和復合型,其中無機型污染比重較大,其污染超標點位數占到了全部污染超標點位的五分之四以上,污染問題突出。我國的土壤污染范圍較廣,總體來看,南方地區土壤污染程度大于北方地區,主要集中在經濟發展水平較高、工業化發達的工礦業周邊、城市及近郊區。土壤污染的蔓延直接觸及我國的生態保護紅線和耕地保護紅線,造成生態環境質量逐漸下降,耕地土壤環境和生產能力嚴重退化。現階段我國土壤污染以重金屬污染為主,受污染耕地總面積1.5億畝,占到了我國18億畝耕地保護紅線的8.3%,耕地質量受損嚴重,造成了巨大的經濟損失。[1]
二、土壤污染的特征和危害
(一)土壤污染的特征
土壤污染作為我國生態環境治理的短板之一,與其他短板相比有不同的特征。土壤污染是進入土壤的污染物含量超過了土壤自身的凈化能力,使土壤內部機理發生質變。第一,土壤污染的來源復雜多樣,涉及大氣,廢水污水、化工用品、重金屬、固體廢棄物、農藥化肥等多方面。第二,土壤污染不容易被察覺,而且形成污染的周期長,滯后性比較突出。第三,土壤污染是污染物在土壤中發生量變的過程,一般污染物進入土壤之后,流動性大大減小,因而不斷沉積從量變引起土壤質變。第四,土壤污染治理困難程度大,治理周期較長,成本較高。[2]
(二)土壤污染的危害
第一,土壤污染通過大氣循環,食物鏈的富集,水環境污染等渠道,經過各種方式進入人類和動植物體內,嚴重影響了人類和動植物的健康。第二,土壤污染制約了我國農業生產的發展,造成農作物減產,農產品質量下降,被間接污染的農產品又直接影響到人類的食品安全。第三,土壤污染影響人類生存空間的環境質量,目前我國發生的多起毒地事件在很大程度上已經引起了人們對土壤污染的重視。第四,土壤污染威脅到我國生態環境安全和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山水林田湖是一個命運共同體,沒有土壤環境的安全就不可能實現生態環境的安全,土壤污染嚴重阻礙了我國現代化建設的進程。[3]
三、土壤污染治理中存在的問題
第一,土壤污染治理法律制度缺失,現階段我國還沒有專門的治理土壤污染的政策或法規,面對目前土壤污染的嚴峻形勢,制定土壤污染防治法及配套政策法規迫在眉睫。第二,土壤污染修復手段單一,技術不成熟,傳統的修復技術難以適應復雜多變的污染狀況,現行的治理手段往往比較單一且效率低,缺乏技術創新,既耗時又耗力。第三,土壤污染管理機制和防治體系不健全,我國土壤污染治理涉及的治理主體多,關系復雜,以往的土壤污染治理中經常出現部門之間相互推諉的情況,造成監管空缺,缺乏統一的管理機制。我國土壤資源種類較多,制定的土壤質量評價標準也多,如何建立一套統一協調的標準體系是今后提高土壤污染治理成效的關鍵。第四,土壤污染治理周期長,資金需求大。由于土壤污染的滯后性、持久性等特點,導致土壤污染治理的周期較長,加之土壤污染的隱蔽性,使社會公眾對土壤污染的重視程度不夠,參與治理土壤污染的積極性不高,這些原因都會增大土壤污染防治成本。[4]
四、土壤污染治理對策
(一)嚴格落實“土十條”,推進土壤污染治理進程
新常態下,美麗中國建設和生態文明建設都對我國的生態環境安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國務院也了《土壤污染防治行動計劃》,土壤污染治理面臨巨大挑戰。《土壤污染防治行動計劃》的為我國土壤污染治理指明了目標和方向,因此必須堅持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理念,嚴格落實“土十條”里的各項任務目標,推進土壤污染治理,改善土壤環境,保障生態環境安全,促進社會和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二)建立健全土壤污染綜合治理的法律體系
面對當前我國土壤污染治理中的種種問題和弊端,必須盡快建立治理我國土壤污染的專門法規,健全土壤污染治理各項配套政策和措施。以立法的方式助推土壤污染治理,明確污染治理主體的職責權限,杜絕污染防治和處理應急事件的過程中相關部門互相推諉的情況。在治理土壤污染的過程中,要強化政府的作用,以政府為主導,加強土壤污染的監管和執法力度,實行污染者付費的制度。
(三)實施土壤污染精準監測機制,完善土壤質量評價標準體系
土壤污染治理的首要前提是全面精準監測和普查全國的土壤污染,建立大數據形式下我國土壤污染監測的信息網絡和數據平臺,建立土壤監測的制度與規范體系,盡快實現我國土壤質量檢測的全覆蓋。要從源頭開始建立土壤污染監測的長效機制,嚴格監督工礦業、農業,水環境、重金屬行業等的污染,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完善土壤質量的評價標準體系。
(四)創新土壤污染修復技術與治理手段,降低治理土壤污染的成本
在治理土壤污染的過程中不斷探索和創新土壤修復的新技術和新方式,加大土壤污染治理的科技投入,改造升級土壤污染治理的設施設備。通過借鑒國外的先進技術和模式,結合我國土壤污染的實際情況,建立多功能、專業的技術研發平臺,不斷優化土壤污染治理模式,完善土壤治理的多元化的投資或融資機制,從根本上降低治理土壤污染的成本。
五、結語
土壤污染治理的成效關系到我國社會和經濟的可持續發展,也關系到人類的健康和生存環境的質量,同時也關系到我國的生態安全和生態文明建設的成敗。加強土壤污染治理和改善土壤環境質量是我國新常態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必然要求,因此必須結合我國實際情況,從社會發展的各個方面著手,重點發力,全面治理,為建設“美麗中國”打下穩固的基礎。
參考文獻:
[1]環境保護部,國土資源部.全國土壤污染狀況調查公報[J].中國環保產業,2014(5):10-11.
[2]陳微,魏君.土壤環境污染現狀分析與對策研究[J].黑龍江科學,2014,5(7):112.
[3]代顯峰.我國土壤污染問題分析及對策研究[J].農業科技與裝備,2013(11):16-17.
第3篇:土壤環境特征范文
關鍵詞:不確定性分析;MonteCarlo模擬;土壤;重金屬
中圖分類號:X820.2 文獻標識碼:A
土壤是歷史自然體,是位于地球陸地表面和淺水域底部具有生命力、生產力的疏松而不均勻的聚積層,基于土壤形成的生態環境體系介于大氣圈、水圈、巖石圈和生物圈的交界面上,是各環境介質的連接紐帶[1].重金屬是一類持久性有毒物,易通過食物鏈的生物放大作用在生物體內積累,從而對人群健康和生態系統的穩定產生危害或風險[2].土壤重金屬污染可改變土壤的理化性質,直接或間接破壞土壤生態系統結構,并可通過土壤農作物等多個途徑的遷移積累對農產品安全和人體健康造成風險,所以土壤環境質量評價作為評估污染程度和制定污染控制策略的重要參考而被廣泛關注.國內外現常用的土壤環境質量評價方法主要包括:單因子指數評價法、內梅羅綜合污染指數法、模糊貼近度法、地累積指數評價法[3]、潛在生態危害指數法[4]等.其中地累積指數評價法是由Muller提出的一種可良好表征土壤中重金屬富集污染程度的定量指標,現廣泛應用于研究評價土壤或沉積物中重金屬的污染程度[5-6].但其在國內外評價過程中仍存在一些缺陷,需要進一步完善,主要表現在:1)常用確定性評價方法中重金屬含量輸入值的單一確定性與評價區域土壤環境中重金屬含量的空間差異性之間的矛盾造成了區域污染評價結果存在較大模糊性;2)不同學者或決策者選取地球化學背景值參數的差異及不同土地利用類型的土壤重金屬背景值的差異造成評價結果缺乏可比性;3)確定性地累積評價模型主要表征土壤中各重金屬的富集污染程度,而忽略了不同重金屬之間的生態毒性差異,這會導致低含量高毒性的重金屬的污染程度被低估或高含量低毒性的重金屬污染程度被高估.以上3點不足均可能會誤導最終決策.
本研究以地累積模型為基礎,將MonteCarlo模擬引入環境質量評價領域中來處理參數不確定性,并在模型內嵌入表征不同重金屬的生物毒性差異的權重系數,提出了基于不確定性理論的土壤環境重金屬污染評價法.將所建土壤環境重金屬污染評價法在實例中加以利用和驗證,以期為土壤重金屬的污染評價、優先污染物的控制及區域污染防控決策的制定提供新思路.
1基于MonteCarlo模擬的評價法
1.1地累積指數評價模型
1.2MonteCarlo模擬的應用
MonteCarlo模擬是由Nicholas Metropolis在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提出的,而后Von Neumann與Stanislaw Ulam合作建立了概率密度函數、反累積分布函數的數學基礎,以及偽隨機數產生器,現此方法在金融工程學、宏觀經濟學、生物醫學、計算物理學等領域已得到應用廣泛,效果良好[7-8].土壤環境評價系統是一個集隨機性、灰性、模糊性等多種不確定性于一體的系統.因此,常規的確定性評價方法不能準確反映土壤中重金屬污染程度的真實情況.為了降低模型參數由于土壤重金屬數據空間變異性、不同學者或決策者采用的地球化學背景值參數的差異性和不同土地利用類型的土壤重金屬背景值的差異性等因素帶來的參數不確定性,本研究將MonteCarlo模擬引入地累積指數法.其主要模擬步驟為[8]:1)確定評價模型隨機變量,在本研究中為土壤中重金屬實測含量參數和其所對應區域土壤背景值參數;2)構建隨機因素的概率分布模型,在本研究中采用歷史經驗和實地采樣檢測相結合的方法;3)將所得到的隨機數轉化為輸入參數的抽樣值,主要方法為MonteCarlo抽樣和拉丁超立方抽樣(LHS).其中MonteCarlo抽樣一般從樣本分布較少的低概率區進行抽樣,即為偏尾端抽樣;LHS抽樣則是由樣本整體分布考慮,這說明相對于MonteCarlo抽樣方法,LHS方法更適合構建小樣本的概率分布,故本文采用LHS法.4)整理分析所得模擬評價結果.
1.3重金屬生物毒性評價權重系數
2實例研究
2.1采樣點布設及樣品采集
實例源于作者2011~2012年的研究成果[10],采樣區域為新鄉市市郊的農用土壤,經過采樣監測所獲數據的統計分析結果見表2.
實際監測數據常包含一些誤差較大的、無代表性的數據,本文建議對所得數據進行異常數據的剔除,否則可能會影響評價區域整體污染水平評價的正確性,本文的剔除原則為平均值±3*標準差[8].本文相關統計計算采用SPSS 16.0vers軟件進行.
將土壤實測含量參數進行ShapiroWilk檢驗,由表2可知,Ni,Zn,Cu和Cr的sig.值均大于0.05,表明這些重金屬的實測含量數據都呈正態分布.而Cd的sig.值小于0.05,不符合正態分布,須進一步轉化驗證,根據其偏度和峰度的信息,選擇Ln函數進行數據轉換,轉換前后的Cd的概率分布見圖2~3所示,故Cd的含量符合對數正態分布.
據上述章節的數據和分析,按照1.2節中的MonteCarlo模擬步驟,將模擬參數設置設定:最大實驗量為1 000,置信區間為95%,抽樣方法為拉丁超立方,其它參數取軟件的默認值.對于實例區域土壤中各種金屬的評價模擬預測圖見圖4~8所示.圖中Probability代表概率可信度,Frequency代表頻數.
根據表1和圖4~8計算得出表4,其表征了各重金屬模擬評價結果隸屬于各污染等級的概率可信度,可得出:1)評價區域重金屬Cd隸屬于嚴重污染等級的概率高達98.1%,對當地有著極大的潛在生態風險或人體健康風險;2)評價區域重金屬Ni和Zn的評價結果較相似,隸屬結果均跨越了全部7個污染等級,說明評價區域中Ni和Zn有著明顯的空間分布特征,同時它們屬于嚴重污染的概率也分別高達84.5%和87%;3)評價區域重金屬Cu的模擬評價結果隸屬于各污染等級的概率較為均勻,其最大隸屬于偏中污染,概率為30.9%,而其隸屬于輕度污染和重度污染的概率分別為21%和24.7%,故很難判斷其最終的評價結論,這也證實了評價過程中確實存在較大的不確定性,并且很可能誤導決策;4)評價區域重金屬Cr的模擬評價結果跨越了3個污染等級,而且它隸屬于輕度污染的可信度達69.8%,這說明Cr的空間含量分布較均勻.
根據單因素指數法的評價準則(評價值大于1則土壤已受污染,小于1則未受污染),可知Cd、Ni和Zn已超標,而Cu和Cr未超標,但單因素指數法只能定性地判斷污染程度,對于篩選優先控制污染物的評價辨識度較低.確定性地累積模型有較為完善的污染程度定量評級準則(見表1),根據表5結果,基本可較好地識別出優先控制污染物,但仍存在一些問題:1)其評價結論中對于Ni和Zn污染等級均為4級,無法進一步分辨二者的相對污染程度的高低;2)Cu和Cr在確定性地累積評價中的污染級別分別為1級和0級,而單因素指數評價中二者的評價結果都小于0(未污染狀態),二種評價方法的結論出現了分歧,故在實際應用中確定性地累積模型的評價分辨力仍有不足.基于MonteCarlo模擬的土壤環境重金屬污染評價結果(IM-C),由于各重金屬潛在生態風險權重系數(Ti)的嵌入,評價結論出現了幾點變化:1)Ni和Zn的IM-C值出現了較顯著的差異,其原因是Ni的潛在生態風險權重系數5遠大于Zn的潛在生態風險權重系數1.大量研究證明Ni具有明顯的致癌性和致敏性,并對水生生物有明顯的危害性[1],相比之下,Zn是人體必不可少的有益元素.這也正對應了我國土壤環境質量標準中關于Ni(60 mg·kg-1)和Zn(300 mg·kg-1)的污染限值差異.參考單因素指數法結果,且對比于確定性地累積法Ni和Zn污染級別一致,證明基于MonteCarlo模擬的土壤環境重金屬污染評價法分辨力更強.2)對比于Zn和Cu的確定性地累積模型評價結果的較大差異,Cu和Zn的IM-C值則相對趨于接近,這是由于Cu的生態風險權重系數5大于Zn的生態風險權重系數1,同樣Cu的污染限值為100 mg·kg-1也明顯嚴于Zn的污染限值300 mg·kg-1,故基于MonteCarlo模擬的土壤環境重金屬污染評價法更符合客觀實際.3)Cu和Cr在確定性地累積模型評價結果中污染等級分別為1級和0級,但根據單因素指數法的評價結果,二者的污染級別都屬于未污染級別,由于Cu的生態風險權重系數大于Cr的生態風險權重系數,基于MonteCarlo模擬的土壤環境重金屬污染評價法“放大”了二者之間評價結果的差異性,更有利于篩選出優先控制污染物.
3結論
針對現行確定性土壤環境質量評價中的不足,提出了基于MonteCarlo模擬和生態風險權重系數的土壤環境重金屬污染評價法,而后借助實例與現行評價方法進行對比研究.結果表明:所提出方法的評價結果為一系列隸屬于各個評價等級的概率可信度,同時,生態風險權重系數的嵌入使其具有更高的評級分辨力.與確定性評價模型相比,能夠更真實、更客觀地表征整體區域土壤中重金屬的真實污染狀態,給決策者提供更全面、科學的參考.
但需要指出,由于所提出的評價方法側重于評價區域整體的土壤重金屬污染水平,所以可能忽略個別極值點,故建議對個別極端值進行確定性污染評價,如評價結果與不確定性評價結果差異較大,則需要有針對性進行采樣調查驗證.
參考文獻
[1]陳懷滿. 環境土壤學[M]. 北京: 科學出版社, 2010.
[2]ZHONG X L, ZHOU S L, ZHU Q, et al. Fraction distribution and bioavailability of soil heavy metals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A case study of Kunshan City in Jiangsu Province, China[J]. Journal of Hazardous Materials, 2011, 198(30): 13-21.
[3]MULLER G. Index of geoaccumlation in sediments of the Rhine river[J]. Geojournal, 1969, 2(3): 108-118.
[4]HAKANSON L. An ecology risk index for squatic pollution control: A sedimentological approach[J]. Water Research, 1980, 14(8): 975-1001.
[5]LU X W, LI L Y, WANG L J, et al. Contamination assessment of mercury and arsenic in roadway dust from Baoji, China[J]. Atmospheric Environment, 2009, 43(15): 2489-2496.
[6]CAEIRO S, COATA M H, RAMOS T B, et al. Assessing heavy metal contamination in Sado Estuary sediment: An index analysis approach[J]. Ecological Indicators, 2005, 5(2): 151-169.
[7]KASTNER M. MonteCarlo methods in statistical physics: Mathematical foundations and strategies[J]. Communications in Nonlinear Science and Numerical Simulation, 2010, 15(6): 1589-1602.
[8]杜本峰. 數據、模型與決策[M]. 北京: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09.
第4篇:土壤環境特征范文
土壤是種養殖農產品主要的環境要素,其承擔著產地環境中大約90%來自各方的污染物[1]。近年來,由于產地土壤環境受到污染而造成的農產品質量安全問題逐漸增多,引起了廣泛的重視和研究[2]。土壤污染具有多源性、隱蔽性、累積性等特性,決定了它對生長在其中的農產品危害的復雜性、長期性、潛在性和突發性[3]。因此,研究產地土壤環境中主要污染物的來源、特點以及污染現狀,提出相應的防治措施,對有效保護我國農產品產地土壤環境,保障農產品質量安全具有重要的意義。
一、產地土壤環境污染的定義及分類
土壤污染的定義目前不統一,主要有3種不同觀點。(1)“絕對性”定義,即部分學者認為由人類向土壤添加有害物質,土壤中該有害物質含量超過了土壤背景值,土壤就受到了污染。(2)“相對性”定義,即有學者以特定的參照數據來加以判斷,如以土壤背景值加2倍標準值為臨界值,如果超過臨界值,則認為土壤已被污染。(3)“綜合性”定義,即定義為不但要看含量的增加,還要看后果,即當加入土壤的污染物超過土壤的自凈能力,或污染物在土壤中累積量超過土壤基準值,而給生態系統造成危害,此時才能被稱為污染。由于第3種定義更具有實際意義,而被使用的最多。土壤污染主要可分為無機物污染(重金屬、化肥、鹽堿類),有機物污染(主要是持久性有機污染物,如多環芳烴、多氯聯苯以及難降解的農藥等有機物質),生物污染(帶有病菌的城市垃圾、廄肥等)以及放射性污染(鍶和銫等在土壤中生存期長的放射性元素)等類型,污染物可單獨對土壤的污染起作用,但多數是多種污染物共存的復合污染。產地土壤環境的污染物來源復雜,但主要來自工礦企業“三廢”污染和污水灌溉兩個方面。據統計,我國耕地污染退化面積約占總耕地面積的1/10,其中工業“三廢”污染的耕地近1000萬hm2,使用污水灌溉的耕地已達330多萬hm2[4]。近年來,農業面源污染也開始成為引起土壤污染的一個重要因素。
二、主要的產地土壤環境污染物
(一)重金屬類物質
目前,國際上公認影響比較大、毒性較高的重金屬類物質一般有5種,即汞、鎘、鉛、鉻、砷。20世紀50-70年代,日本富士縣的“骨痛病”就是由于鎘污染而導致糙米中鎘超標而引起的,患者數千人,其中數百人死亡,至今還有人不斷提出和索賠。隨著我國工業和農業的快速發展,城市化進程的不斷加快,由于污水灌溉和工礦企業排污引起的產地土壤環境重金屬污染問題也逐漸顯現。如我國20世紀70年代,就有學者研究發現遼寧省沈陽張士灌區的土壤重金屬超標嚴重,污染面積達2500多hm2,造成農產品無法食用[5]。雷鳴等人對湖南工礦污染區的調查也顯示,株洲和湘潭等地工礦污染地區的鎘、砷和鉛污染面積占當地耕地總面積的90%以上[6]。在各類農產品中,水稻和葉菜類蔬菜是最易富集重金屬元素的農作物[7~8],因此,當土壤被環境中的重金屬污染后,稻米和葉菜類蔬菜中重金屬殘留問題值得關注。重金屬污染普遍具有以下共同點:(1)污染面積逐漸擴大。由于重金屬類物質與污染排放密不可分,隨著工農業的快速發展,特別是重工業的地域性轉移,重金屬元素威脅的范圍逐漸加大。(2)污染治理耗時較長。土壤中的重金屬很難靠稀釋作用和自凈化作用來消除,即使通過生物修復等手段,某些被重金屬污染的土壤也可能要100~200年時間才能夠恢復。(3)累積性和不可逆性。土壤中的重金屬會被農作物吸收,通過食物鏈逐級放大和改變存在形態,從而對人體健康造成嚴重威脅。比如,汞被生物體甲基化后形成甲基汞,其具有神經毒性的環境污染物,主要侵犯中樞神經系統,可造成語言和記憶能力障礙等嚴重問題。人體長期攝入重金屬,會蓄積于內臟和骨骼中,引起多種疾病。如在人體內,鎘的半衰期長達7~30年,可蓄積50年之久,能對多種器官和組織造成損害[9]。如此長的半衰期,對人體來說甚至是不可逆的,一旦進入體內就難以排出。
(二)持久性有機污染物(POPs)
POPs是指一類具有長期殘留性、生物蓄積性、半揮發性和高毒性,能夠在大氣環境中長距離遷移并能沉積回地球,對人類健康和環境具有嚴重危害的天然或人工合成的有機物質。目前,我國污染較為嚴重的POPs物質主要有:(1)多環芳烴(PAHs)。我國已有學者開展了對京津及附近地區、長三角地區、珠三角地區及東南沿海等區域的研究。結果表明,土壤中的PAHs主要來源于燃燒源(包括工業燃煤、汽車尾氣排放等)。對北京郊區土壤中16種PAHs的研究表明,土壤中16種PAHs的平均濃度為1350μg/kg,其含量范圍在16~3880μg/kg之間[10]。(2)有機氯農藥(OCPs)。OCPs具有高效的殺蟲力,1950-1970年被廣泛用于農業生產,但是由于OCPs特殊的物理化學性質,其難以被化學降解和生物降解,在土壤中半衰期可達幾年甚至十幾年。由于OCPs嚴重對環境的影響,從20世紀80年代起許多國家開始禁止或限制使用OCPs。據統計,我國多年來累計施用滴滴涕40多萬t,六六六等OCPs19萬余t,雖然OCPs目前已被禁止使用,但是由于降解緩慢,其對土壤的污染仍不容小視[11~12]。(3)二英(Dioxin)。二英是一類物質的簡稱,包括210多種化合物。焚燒垃圾和塑料制品,以及有機物和氯的熱處理過程,都會釋放二英類物質。它們通過大氣干濕沉降、污水污泥農用以及廢棄物堆放等多種途徑進入土壤環境[13]。我國有學者對一些地區土壤中二英含量的調查顯示,部分省份土壤存在二英污染問題,其中鋼鐵廠和垃圾焚燒廠周圍土壤污染尤為明顯[14~16]。(4)多氯聯苯(PCBs)。PCBs不但具有持久性有機污染物高毒、難降解的共同特點,同時還是內分泌干擾物,對人類健康和環境具有嚴重危害。目前,在工業發達的國家和地區,已發現有較高濃度的PCBs。在不發達國家和地區、人跡罕至的海洋、大氣、水、土壤中也發現了PCBs。我國從1965年開始生產PCBs,到20世紀80年代初停產,共生產上萬t,多年的使用造成一些地區環境污染嚴重[17],已經在局部地區釀出了嚴重污染事件。POPs污染的主要特點:(1)高毒性。主要表現為它的“三致性”,即致癌、致畸、致突變效應。它還具有遺傳毒性,能造成人體內分泌系統紊亂,使生殖和免疫系統受到破壞,并誘發癌癥和神經性疾病。(2)持久性。POPs類有機污染物結構穩定,在自然條件下很難被降解。研究表明,即使是很多年前使用過,在許多地方依然能夠發現它們的殘留物,POPs分子結構中化學鍵具有相對較高的鍵能,可以抵御光解、化學和生物降解。一旦它們釋放進入環境,將有可能在環境中持久存在。(3)生物蓄積性。POPs類有機污染物分子結構中通常含有鹵素原子,具有低水溶性、高脂溶性的特征,因而能夠在脂肪組織中發生生物蓄積,從而導致從周圍介質遷移、富集到生物體內,并通過食物鏈的生物放大作用達到中毒濃度。(4)遷移性。POPs具有半揮發性,能夠從水體或土壤中以蒸汽形式進入大氣環境或被大氣顆粒物吸附,通過大氣環流遠距離遷移。在較冷或高海拔地方會重新沉降到地面上。而后在溫度升高時,它們會再次揮發進入大氣,進行遷移。如今在地球兩極以及珠穆朗瑪峰地區都已監測到POPs物質的存在。
(三)農業面源污染物質
農業面源污染主要是在農業生產過程中濫施化肥、農藥和農用地膜所致。(1)化肥。自從1843年人類開始生產化肥以來,化肥的使用已有165年的歷史,隨著農業的發展,全球化肥施用量將不斷增加。我國自20世紀80年代開始,化肥施用量逐年增長。農業部數據顯示,目前使用量約穩定在5460萬t(折純量),平均施用量達500kg/hm2以上,遠遠超出發達國家225kg/hm2的安全上限。由于化肥主要來源于礦物,其中含有大量的重金屬類物質,比如用作磷肥的礦石中通常含有一定量的鎘元素,過量施用必然會造成間接污染。(2)農藥。雖然有機氯等高殘留農藥目前已被禁止,但其他農藥使用問題也非常突出。據統計,2006年我國農藥年產量約130萬t,使用面積約2.8億hm2,只有約20%能被作物吸收利用,大部分進入了水體、土壤及農產品中[18~19]。除有效成分外,農藥中的助劑等其他成分也會長期殘留于產地土壤環境中,形成持續污染。(3)農用地膜。由于設施農業的普及,地膜污染也在加劇,近20年來,我國的地膜用量和覆蓋面積已居世界首位,2010年地膜覆蓋面積約為1.8×1011m2,年用量約為130萬t,年均約有50萬t農膜殘留于土壤中,殘膜率達40%。而且在全部農膜市場中,高檔農膜僅占2%,中低檔農膜高達98%[20]。殘留土壤中的劣質地膜不但破壞土壤結構,減低土壤肥力,還會在分解過程中析出鉛、錫等有毒物質,影響作物安全。面源污染的主要特點:(1)影響面積大。與重金屬污染等集中于工礦企業周邊不同,面源污染物質影響面積非常大[21]。據統計,我國化肥利用率不到4成,在施用過程中,大量肥料未被有效利用并流失,這在我國幾乎所有耕地中都會產生。(2)直接危害小。大多數面源污染物主要影響水體環境,對產地土壤環境的直接危害較小,其危害主要表現在間接方面,即長期過量使用化肥會出現土壤孔隙堵塞、板結甚至酸化,降低微生物活性,從而降低農作物產量,同時能活化重金屬等有害物質,影響農產品質量安全。(3)污染控制難。農業面源污染的污染源并不具體,同時在給定的區域內它們的排放是相互交叉的,加之不同的地理、氣象、水文條件對污染物的遷移轉化影響很大,因此很難具體監測單個污染源的排放并加以控制。
三、我國產地土壤環境污染的主要問題分析
(一)污染源頭控制不到位
由于我國部分企業環保意識不強,污染控制技術不達標,工業“三廢”和污水灌溉造成的產地土壤環境污染并未禁絕,污染事故仍時有發生。同時,由于我國環境管理體系主要建立在城市和重要點源污染防治上,對面源污染重視不夠,導致農村環境治理體系的發展嚴重滯后。加之農業投入品使用方式粗放,缺乏科學引導,特別容易導致農業面源污染,使目前畜禽養殖業和礦物肥料大量施用造成的產地土壤環境污染問題逐步顯現。
(二)污染底數不清楚
目前我國產地土壤環境污染途徑多,原因復雜,由土壤污染引發的農產品安全事件時有發生,成為影響農業生產、群眾健康和社會穩定的重要因素。而現在已開展的污染監測工作覆蓋范圍較窄,對產地土壤污染的范圍、程度甚至污染物種類缺乏整體的掌握,導致防治缺乏針對性。
(三)污染治理缺乏有效手段
產地土壤環境污染治理的難度較大,其主要原因在于土壤本身的結構復雜,且各地土壤背景情況各不相同,對污染物的結合情況多變,加之復合污染物之間的相互作用,使得快速解決土壤污染問題難以實現。土壤污染修復的方法多種多樣[22],包括物理方法,如客土法、熱處理法等,缺點在于費用昂貴,難以用于大規模污染土壤的改良。化學方法,如化學固定或化學淋洗等,但前者只能降低污染物的生物有效性,后者又容易造成二次污染。生物修復方法,其中植物修復以運行成本低,回收和處理富集重金屬的植物較為容易,成為了近年來發展的熱點,但該方法的主要問題在于超積累植物較難獲得,同時植物對重金屬一季累積的絕對量并不可觀。
四、產地土壤環境污染的防治對策建議
(一)杜絕污染源頭
消除工業“三廢”對產地的污染排放,嚴格污灌管理。加大環保監管和執法力度,嚴格執行國家制定的污染排放標準,杜絕超標排放現象。特別注重產地環境的保護工作,設立定位監測點,健全農業環境監測網絡。同時,嚴格控制農業面源污染。應加大對農業面源污染的重視程度,加強農業環境法律法規建設,完善農村環境管理機構。積極轉變農業發展方式,推進測土配方施肥、精準施肥、水肥一體化等農業技術,鼓勵使用農家肥或其他有機肥料,提高化肥利用率,從源頭上減少化肥流失造成的面源污染。
(二)做好農產品產地土壤環境治理規劃和分級工作
農產品產地土壤環境污染往往呈現時空變異性,同時由于污染物種類繁多,潛在的相互作用等因素,難以簡單界定。因此,應積極開展農產品產地土壤環境的小比例尺詳細普查數據,摸清污染原因、污染種類和范圍程度,做好治理的規劃計劃。同時,健全產地土壤環境標準,組織開展污染等級劃分工作,對未污染的土壤,要進一步加大保護力度;對輕度污染的土壤,應抓緊修復治理或種植替代作物;對有毒有害物質超標嚴重的土壤,應堅決設立禁止生產區,或科學調整種植其他非食用農作物。
第5篇:土壤環境特征范文
>> 淮南謝橋塌陷區表層土壤重金屬污染分布特征與現狀評價研究 城市表層土壤重金屬污染分析 城市表層土壤重金屬污染分析模型 基于因子分析法的城市表層土壤重金屬污染模型 關于城市表層土壤重金屬污染的數學模型分析 城市表層土壤重金屬污染的因子分析 城市表層土壤重金屬污染來源與分布問題 利用高斯模型和尺度空間理論分析表層土壤重金屬污染 表層土壤重金屬污染源的分析方法 基于表層土壤重金屬污染分析的數學模型 貴州麥西河沉積物及土壤中重金屬分布特征及污染評價 城市表層重金屬污染的綜合評價 成都平原典型菜園土重金屬含量的空間分布特征 海南昌化鉛鋅礦廢棄地重金屬污染評價及其空間分布特征 臥龍湖沉積物中典型重金屬污染評價及其空間分布特征 地表層土壤重金屬污染傳播模型 灌溉水—耕作土壤—化肥—作物生態系統中重金屬鎘的分布特征 煤矸石充填型重構土壤中重金屬的生物遷移及分布特征 商洛茶葉和產地土壤重金屬元素含量及分布特征研究 畜禽養殖廢水灌溉土壤中重金屬分布特征研究 常見問題解答 當前所在位置:l,2011-09-09.
[2] 范拴喜,甘卓婷,李美娟,等.土壤重金屬污染評價方法進展[J].中國農學通報,2010,26(17):310-315.
[3] 張堯庭,方開泰.多元統計分析引論[M]. 北京:科學出版社,1982.
[4] 劉 靜,蔡國學,劉洪斌.西南丘陵地區土壤有機質含量的空間插值法研究[J].西南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2008,30(3):107-111.
[5] 吳學文,晏路明.普通Kriging法的參數設置及變異函數模型選擇方法――以福建省一月均溫空間內插為例[J].地球信息科學,2007,9(3):104-108.
[6] 張朝生,章 申,等.長江水系河流沉積物重金屬元素含量的計算方法研究[J].環境科學學報,1995,15(3):258-264.
[7] 劉付程,史學正,于東升,等.基于地統計學和GIS的太湖典型地區土壤屬性制圖研究――以土壤全氮制圖為例[J].土壤學報,2004,41(1):63-70.
[8] 國家環境保護局.中國土壤元素背景值[M].北京:中國環境科學出版社,1990.
[9] 劉鳳枝.農業環境監測實用手冊[M].北京: 中國標準出版社,2001.
[10] GB15618-1995,土壤環境質量標準[S].
[11] 尹 君.基于GIS 綠色食品基地土壤環境質量評價方法研究[J].農業環境保護,2001,20(6):10-11.
[12] 陳俊堅,張會華.廣東省區域地質背景下土壤表層重金屬元素空間分布特征及其影響因子分析[J].生態環境學報,2011, 20(4):646-651.
[13] 張長波,李志博,姚春霞,等.污染場地土壤重金屬含量的空間變異特征及其污染源識別指示意義[J].土壤學報,2006, 38(5):525-533.
第6篇:土壤環境特征范文
關鍵詞:土壤;重金屬;污染特征;污染評價;果蔗地
中圖分類號:X5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0439-8114(2017)07-1262-05
DOI:10.14088/ki.issn0439-8114.2017.07.015
Content Characteristics and Risk Assessment of Heavy Metals in Chewing Cane Soils
WANG Tian-shun, YANG Yu-xia, LIAO Jie, FAN Ye-geng, YA Yu, ZHU Jun-jie, MO Lei-xing
(Research Institute of Agro-products Quality Safety and Testing Technology, Guangxi Academy of Agriculture Sciences/Quality Supervision and Testing Center for Sugarcane, China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Nanning 530007, China)
Abstract: The contents of soil heavy metals,such as Cd,Pb,Cr,Cu,Zn,As and Hg,in surface soil(0~20 cm) from the main chewing cane production farmland in Guangxi Zhuang Autonomous Region,were investigated. Poll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heavy metals in soils were observed on the basis of environmental quality secondary standard values of single factor pollution index method and comprehensive pollution index method. Potential ecological risk assessment was evaluated by using the geoaccumulation index(Igeo) and potential ecological risk index(RI).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average concentrations of Cd,Pb,Cr,Cu,Zn,As and Hg were 0.81,30.4,54.5,29.8,107.4,16.69 and 0.28 mg/kg,respectively. According to the comprehensive pollution index,the pollution degree was middle degree with PN was 2.03. According to the geoaccumulation index,the pollution degree of Cd was middle degree with Igeo was 1.02,and Hg ranged from light to middle degree with Igeo was 0.30. The potential ecological risk index indicated that the heavy metals in the soils from research area were at the moderate ecological hazard level. The rate of contribution for Cd was the highest to potential ecological risk index. Thus,effective farmland soil management is necessary to ensure security production, control soil pollution sources,and implement standard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Key words: soils; heavy metals; contaminant characteristics; risk assessment; chewing cane soil
土壤是人類賴以生存的自然資源,也是人類生態環境的重要組成部分。重金屬在自然環境中廣泛存在,因其持久性、積累性等特性及其對生態環境存在的潛在風險,受到國內外學者的高度關注[1,2],土壤重金屬污染已經成為當前人類面臨的重要環境問題,也是目前環境科學領域的研究熱點之一[3-6]。土壤重金屬污染來源包括礦山采選冶煉、大氣沉降、污水灌溉、固體廢棄物堆存與處置、交通運輸等[7,8]。當土壤中重金屬達到一定的累積程度時,會通過食物鏈傳遞到動物和人體內,給生態環境及人體健康造成很大危害[9,10]。
近年來,果蔗生產中大量使用農藥、磷肥、污水,使得果蔗地土壤-植物系統中重金屬污染更為復雜與多樣化。土壤是植物生長的載體,其清潔程度直接影響著食物中有毒有害物質的濃度,目前對果蔬、糧食產地[11,12]中重金屬的污染評價己有不少報道,但針對果蔗地土壤重金屬污染的系統研究鮮有報道。為了解廣西壯族自治區橫縣果蔗種植區土壤質量狀況,本研究以果蔗地土壤為對象,利用單因子污染指數法、綜合污染指數法、地積累指數法和潛在生態風險指數法對土壤重金屬的污染特征及生態風險進行評價,同時探討了各重金屬元素之間的相關性和聚類狀況,以期為廣西壯族自治區果蔗地土壤重金屬的污染防治和治理提供科學依據。
1 材料與方法
1.1 樣品采集與分析
土壤樣品全部采自廣西壯族自治區果蔗地0~20 cm表層土壤。于2014年11月選取36個采樣點,每個樣點600~1 300 m2內采用W形布點采集5個子樣,現場剔除植物根系、碎石等雜物后充分混合組成一個混合樣品,用四分法縮分至約4.0 kg,裝入聚乙烯塑料袋,貼好標簽,帶回實驗室備用。把采集的土壤置于寬敞、干凈、透氣的室內,均勻攤開,自然風干,去除石塊、植物根系及其他的雜物后用瑪瑙研缽研磨后過2 mm尼龍篩,再用瑪瑙研缽繼續研磨后過100目篩。
稱取0.200 0 g經風干處理的土樣于聚四氟乙烯罐中。加5 mL HNO3、3 mL HCl、1 mL H2O2和1 mL HF,密封消解罐后放入微波消解爐。消解程序分3步,步驟1為160 ℃、90%功率消解10 min;步驟2為200 ℃、90%功率消解25 min;步驟3為100 ℃、40%功率消解5 min。消解完室溫放置后,轉移消解罐中的溶液于聚四氟乙烯燒杯中,加熱蒸發去除氮氧化物。剩余液體做如下處理:①轉移至100 mL容量瓶,用1%硝酸稀釋至刻度線,混合均勻后用石墨爐原子吸收儀(MKⅡ MQZ,美國Thermo)測定溶液中Cd、Pb的含量、用火焰原子吸收儀(AA240,美國Varian)測定Cr、Cu、Zn的含量;②轉移至50 mL容量瓶,加入5 mL 50 g/L硫脲和50 g/L抗壞血酸溶液作掩蔽劑,用5%鹽酸稀釋至刻度線,混合均勻,室溫下靜置30 min后用原子熒光光譜儀(AFS-230E,北京海光儀器公司)測定As和Hg的含量。
試驗所用試劑均為優級純試劑,用水均為超純水。
1.2 土壤重金屬污染評價
土壤評價標準采用GB 5618-1995《土壤環境質量標準》[13]中的二級標準和廣西土壤背景值[14],采用單因子污染指數、內梅羅綜合污染指數法、地積累指數法以及潛在生態危害指數法分別對土壤重金屬污染狀況進行評價。采用Excel 2007和DPS軟件對數據進行統計分析。
1.2.1 單因子污染指數法 單因子污染指數法是用來評價單個污染因子對土壤的污染程度,污染指數愈小,說明該因子對環境介質污染程度愈輕[15,16]。其計算公式如下:
Pi=Ci/Si
式中,Pi為土壤中重金屬的污染指數,具體反映某污染物超標倍數和程度;Ci為土壤中重金屬含量的實測值(mg/kg);Si為土壤中重金屬的標準限定值(mg/kg)。當Pi≤1時,表示樣品未受污染;當Pi>1 時,表示樣品已被污染。Pi的值越大,說明樣品受污染越嚴重。Pi評價標準見表1。
1.2.2 綜合污染指數法 綜合污染指數法[17,18],即內梅羅污染指數,是將目標單個污染指數按一定方法綜合起來考慮對環境介質的影響程度,采用兼顧單元素污染指數平均值和最大值的一種評價方法。其計算公式如下:
PN=■
式中,Piave為土壤中各重金屬污染指數的平均值;Pimax為土壤中單項重金屬的最大污染指數;PN為采樣點的綜合污染指數,其評價標準見表1。該方法突出了高濃度污染物對土壤環境質量的影響,能反映出各種污染物對土壤環境的作用,將研究區域土壤環境質量作為一個整體與外區域或歷史資料進行比較。
1.2.3 地積累指數法 地積累指數(Igeo)是德國海德堡大學沉積物研究所的科學家Müller[19]提出的一種研究沉積物中重金屬污染的定量指標,在歐洲被廣泛采用。該方法在考慮自然地質過程造成背景值影響的同時,充分考慮了人為活動對重金屬污染的影響,因此該指數不僅可以反映沉積物中重金屬分布的自然變化特征,而且可以判別人為活動對環境的貢獻[20,21]。其計算公式為:
Igeo=log2[Cn/(1.5×Bn)]
式中,Cn為樣品中元素n在沉積物中的實測值;Bn為沉積物中該元素的地球化W背景值,本研究采用廣西壯族自治區土壤環境背景值作為參照標準;1.5為修正指數,用于校正區域背景值差異。地積累指數劃分為7級,Igeo≤0,為1級,無污染;0
1.2.4 潛在生態危害指數法 重金屬元素是具有潛在危害的重要污染物,與其他污染物的不同之處在于它們對環境危害的持久性、生物地球化學的可循環性及潛在的生態危害。潛在生態危害系數法是瑞典科學家Hakanson[22]提出的一種沉積物中重金屬的評價方法,為了使區域質量評價更具有代表性和可比性,該方法從重金屬的生物毒性角度出發,反映了多種污染物的綜合影響[23,24]。土壤中多種重金屬元素潛在生態危害指數是各單一重金屬元素的潛在生態危害指數之和。其計算公式如下:
RI=■Eri
Eri=Tri×Csi/Cni
式中,Csi為表層土壤重金屬元素i的分析測量值;Cni為土壤重金屬元素i的參比值,本研究采用廣西壯族自治區土壤環境背景值作為參照標準;Tri為重金屬元素毒性系數[25],各重金屬的毒性系數分別為Cd=30,Pb=Cu=5,Cr=2,Zn=1,As=10,Hg=40[26]。Eri為單個重金屬的潛在生態危害指數;RI為多種重金屬綜合潛在生態危害指數。重金屬污染的生態危害指數分級標準見表2。
2 結果與分析
2.1 研究區土壤重金屬含量特征
研究區36個土壤樣品的重金屬元素的含量范圍、均值、標準差等特征參數見表3。需要說明的是,有32個土壤樣品土壤呈酸性,4個土壤樣品土壤呈弱堿性。研究區土壤中Cd、Pb、Cr、Cu、Zn、As和Hg的平均含量分別為0.81、30.4、54.5、29.8、107.4、16.69、0.28 mg/kg,除了Cr和As外,其他5種重金屬平均含量均超過廣西土壤背景值,分別為土壤背景值的3.03、1.27、1.07、1.42、1.84倍。
7種重金屬的標準差除Cd和Hg外,其他均較大;Cr、Zn的標準差在15以上,Pb的標準差為9.37,As的標準差為5.97,Cu的標準差為5.20。說明重金屬的分布不均勻,甚至有的重金屬分布極不均勻。土壤中7種重金屬的變異系數從大到小的順序依次為Hg、Cd、Cr、As、Zn、Pb、Cu,其中,Hg、Cd變異系數分別為48.3%、46.1%,說明Hg和Cd受人為活動干預強烈,其次為Cr、As、Zn,Cu的變異系數最小,表明在整個研究區域Cu含量相對比較均一。
2.2 土壤重金屬污染評價
2.2.1 單因子污染指數與綜合污染指數評價 研究區土壤重金屬單因子污染指數見表4。結果表明,研究區土壤中重金屬Cd、Pb、Cr、Cu、Zn、As和Hg單因子污染指數的平均值分別為2.73、0.61、0.36、0.55、0.53、0.44和0.88。按照土壤環境質量二級評價分級標準,土壤樣品中重金屬元素Cr、Cu、Zn、As單因子污染指數均小于1,屬于安全等級。重金屬元素Cd、Pb和Hg單因子污染指數達到輕污染水平的樣本占樣本總數的19.4%、2.8%和30.6%;Cd和Hg單因子污染指數達到中污染水平的樣本分別占樣本總數的11.1%和2.7%;Cd單因子污染指數達到重污染水平的樣本占樣本總數的58.3%。
采用綜合污染指數法對采樣點土壤中Cd、Pb、Cr、Cu、Zn、As和Hg 7種重金屬元素污染狀況進行綜合評價,由各單因子污染指數計算可知,采樣點的綜合污染指數值為2.03,污染等級屬于中污染。
2.2.2 地積累指數法評價 地積累指數法是從地球化學的角度出發來評價土壤中重金屬的污染。它除了考慮到人為污染因素、環境地球化學背景值外,還考慮到由于自然成巖作用可能會引起背景值變動的因素,它所采用的背景值一般為未受人類活動影響的沉積巖中的地球化學背景值,因此該方法更多的強調了土壤中重金屬污染的歷史累積作用。由表5可知,果蔗地土壤中Cd的污染程度相對比較嚴重,污染等級為3級,污染程度達中等污染;其次是Hg,污染等級為2級,其污染程度達輕-中等污染;Pb、Cr、Cu、Zn和As均屬于無污染。7種重金屬的污染程度順序依次為Cd>Hg>Zn>Pb>Cu>As>Cr。
2.2.3 潛在生態危害評價 潛在生態危害指數法是從沉積學角度出發,它不僅考慮了土壤重金屬含量,而且將重金屬的生態效應、環境效應與毒理學聯系在一起,因此其評價結果主要反映了人類活動對土壤的潛在生態危害。由表6可知,從單個重金屬的潛在生態危害系數來評價,果蔗地土壤的主要潛在生態危害重金屬為Cd和Hg,Cd污染達到強生態危害程度,Hg污染達到中等生態危害程度,其他5種重金屬均為輕微生態危害程度,其潛在生態危害順序為Cd>Hg>As>Pb>Cu>Zn>Cr。綜合潛在生態危害指數達到187.27,處于中等生態危害程度。
2.3 研究區土壤重金屬含量相關分析
研究區土壤中重金屬之間的相關性可以推測重金屬的來源是否相同,若它們之間存在相關性,則它們的來源可能相同,否則來源可能不同[16]。利用DPS軟件對各重金屬進行相關性分析,在0.05和0.01 顯著性水平下,所有變量間相關系數如表7所示。As與Cd、Cr、Cu、Zn之間存在極顯著正相關,表明As和Cd、Cr、Cu、Zn之間緊密相關;Zn與Cr、Cu之間存在極顯著正相關;Cu與Cr之間存在極顯著正相關,Cu與Pb之間存在極顯著負相關;Cd與Cr之間存在極顯著正相關。相關性結果可以說明研究區域土壤重金屬As與Cd、Cr、Cu、Zn同源性很高,與果蔗栽培管理過程中污水的灌溉、污泥的施用及重金屬農藥的施用有關,Hg與其他重金屬元素之間沒有明顯的相關性,說明研究區域Hg含量受人為活動的影響強烈,有外源污染M入。
2.4 研究區土壤重金屬聚類分析結果
利用DPS軟件對研究區各重金屬進行聚類分析,結果如圖1所示。由圖1可知,7種重金屬共分為5組,第一組為Pb和Cu;第二組為As;第三組為Cr;第四組為Cd和Hg,它們的潛在生態危害指數分列前2位;第五組為Zn。Pb和Cu、Cd和Hg是距離較近且潛在生態危害指數值接近,分別被聚為一類。
3 結論
研究區域土壤重金屬Cd、Pb、Cr、Cu、Zn、As和Hg的平均含量水平分別為0.81、30.4、54.5、29.8、107.4、16.69、0.28 mg/kg。利用《土壤環境質量標準》二級標準進行評價,結果顯示Cd污染最嚴重,單因子污染指數最高為4.93;Hg污染次之。
重金屬地積累指數評價結果表明,果蔗地土壤中Cd的污染程度相對比較嚴重,污染等級為3級,污染程度達中等污染;其次是Hg,污染等級為2級;潛在生態危害綜合指數評價結果顯示,果蔗地土壤中重金屬污染處于中等生態危害程度,其土壤的主要潛在生態危害重金屬為Cd和Hg,Cd污染達到強生態危害程度,Hg污染達到中等生態危害程度。
土壤中7種重金屬的相關性分析表明,研究區域土壤重金屬As與Cd、Cr、Cu、Zn具有同源性,與果蔗栽培管理過程中污水的灌溉、污泥的施用及重金屬農藥的施用有關;聚類分析表明,Pb和Cu、Cd和Hg距離較近且污染指數值接近,分別被聚為一類。
廣西壯族自治區果蔗地土壤重金屬污染來自多種污染源,筆者認為土壤重金屬累積的原因主要是各種含重金屬農用物資的投入、污水灌溉及污泥施用等。對被污染土壤應采取一些農業、生物及施用一些改良劑等措施進行綜合修復、治理,以確保生態環境及果蔗產品的安全。
參考文獻:
[1] NIU L L,YANG F X,XU C,et al. Status of metal accumulation in farmland soils across China:From distribution to risk assessment[J].Environmental Pollution,2013,176:55-62.
[2] MAPANDA F,MANGWAYANA E N,NYAMANGARA J,et al. Uptake of heavy metals by vegetables irrigated using wastewater and the subsequent risks in Harare,Zimbabwe[J].Physics Chemistry of the Earth,2007,32(15-18):1399-1405.
[3] 胡國成,張麗娟,齊劍英,等.貴州萬山汞礦周邊土壤重金屬污染特征及風險評價[J].生態環境學報,2015,24(5):879-885.
[4] 麻冰涓,王海鄰,李小超,等.豫北典型農田作物中重金屬污染狀況及健康風險評價[J].生態環境學報,2014,23(8):1351-1358.
[5] 張洪偉,張國珍,張克江,等.黃河蘭州段黃灌區蔬菜大棚土壤重金屬含量分析及污染評價[J].土壤通報,2012,43(6):1497-1501.
[6] 韓 平,王紀華,馮曉元,等.北京順義區土壤重金屬污染生態風險評估研究[J].農業環境科學學報,2015,34(1):103-109.
[7] 陳 濤,常慶瑞,劉 京,等.長期污灌農田土壤重金屬污染及潛在環境風險評價[J].農業環境科學學報,2012,31(11):2152-2159.
[8] 郭 偉,趙仁鑫,張 君,等.內蒙古包頭鐵礦區土壤重金屬污染特征及其評價[J].環境科學,2011,35(10):3099-3105.
[9] HE B,YUN Z J,SHI J B,et al. Research progress of heavy metal pollution in China: Sources,analytical methods,status,and toxicity [J].Chinese Science Bulletin,2013,58(2):134-140.
[10] KHAN K,LU Y L,KHAN H,et al. Heavy metals in agricultural soils and crops and their health risks in swat district, northern Pakistan [J].Food and Chemical Toxicology,2013,58:449-458.
[11] KHAN S,CAO Q,ZHENG Y M,et al. Health risks of heavy metals in contaminated soils and food crops irrigated with wastewater in Beijing,China[J].Environmental Pollution,2008, 152(3):686-692.
[12] 秦普S,劉 麗,侯 紅,等.工業城市不同功能區土壤和蔬菜中重金屬污染及其健康風險評價[J].生態環境學報,2010,19(7):1668-1674.
[13] GB 15618-1995,土壤環境質量標準[S].
[14] 廣西環境保護科學研究所.土壤背景值研究方法及廣西土壤背景值[M].南寧:廣西科學技術出版社,1992.
[15] 胡 明.大荔縣農田土壤重金屬分布特征與污染評價[J].干旱區資源與環境,2014,28(1):79-84.
[16] 程 芳,程金平,桑恒春,等.大金山島土壤重金屬污染評價及相關性分析[J].環境科學,2013,34(3):1062-1066.
[17] 張鵬巖,秦明周,陳 龍,等.黃河下游灘區開封段土壤重金屬分布特征及其潛在風險評價[J].環境科學,2013,34(9):3654-3662.
[18] YUAN G L,SUN T H,HAN P,et al. Source identification and ecological risk assessment of heavy metals in topsoil using environmental geochemical mapping: Typical urban renewal area in Beijing,China[J].Journal of Geochemical Exploration, 2014,136(1):40-47.
[19] M?BLLER G. Index of geoaccumulation in sediments of the Rhine River[J].Geological Journals,1969,2:109-118.
[20] 范拴喜,甘卓亭,李美娟,等.土壤重金屬污染評價方法進展[J].中國農學通報,2010,26(17):310-315.
[21] 孔慧敏,左 銳,滕彥國,等.基于地球化學基線的土壤重金屬污染風險評價[J].地球與環境,2013,41(5):547-552.
[22] HAKANSON L. An ecological risk index for aquatic pollution control:A sedimentological approach[J].Water Research,1980, 14(8):975-1001.
[23] 朱蘭保,盛 蒂,戚曉明,等.蚌埠龍子湖底泥重金屬污染及生態風險評估[J].安全與環境學報,2013,13(5):107-110.
[24] 王大洲,胡 艷,李 魚.某陸地石油開采區土壤重金屬潛在生態風險評價[J].環境化學,2013,32(9):1723-1729.
第7篇:土壤環境特征范文
關鍵詞:土壤污染;生態環境;環境治理;污染防治。
隨著我國工業化進程加速、城市化的大力推進以及化學品、農藥等現代科技產品的使用,人類社會向自然環境排放了大量污染物,使得土壤污染的總體形勢異常嚴峻。我國在土壤污染防治方面立法供給嚴重不足,現有立法呈現分散碎片的特征,遠不能滿足土壤污染防治的現實需要,我國亟需系統化完善土壤污染防治立法。
一、我國土壤生態環境現狀。
土壤是“以母質為基礎,在物理、化學和生物的長期共同作用下,不斷演化而成的土狀物質,它由固相、液相和氣相物質以及生物體四部分組成,各部分之間相互作用,形成了一個復雜的體系”。[1]土壤是生態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動植物生長繁育的自然基礎之一。土壤各組成部分互相聯系、互相作用,共同組成了復雜多樣的土壤生態環境系統。土壤生態環境系統內外存在著物質、能量和信息的變化與交換,保持著結構和功能的動態穩定。土壤結構多樣、功能多元和過程復雜的特性使得土壤對人類具有極其重要的經濟價值和生態價值。然而,土壤生態環境系統卻非常脆弱,土壤具有吸附性、緩沖性、氧化還原性以及自凈的功能,其能廣泛接觸水、大氣、固體廢物等中的污染物,這就使得土壤極易受到污染。
土壤污染是指“由人類活動產生的各種污染物通過各種途徑輸入土壤,其數量和速度超過了土壤的凈化能力,導致土壤的組成、結構和功能等發生變化,從而使土壤的生態平衡受到破壞,正常功能失調,導致土壤環境質量下降,影響作物的正常生長發育,并產生一定的水和大氣次生污染的環境效應,最終將危及人體健康以及人類生存和發展的現象。”[2]我國土壤污染的總體形勢相當嚴峻,據不完全統計,“目前中國受污染的耕地約有 1.5 億畝,污水灌溉污染耕地 3250 萬畝,固體廢棄物堆存占地和毀田 200 萬畝,合計約占耕地總面積的 1/10 以上”[3]。這些土壤污染的污染源主要有酸雨、大氣塵埃、工礦固體廢物、生活垃圾、化肥和農藥、工礦廢水灌溉、農家肥、地膜污染等。與大氣污染、水污染相比,土壤污染具有隱蔽性、富集性、復雜性和不易逆轉性的特點,這使得土壤污染的危害嚴重,治理困難、耗資巨大。
土壤污染對人體健康、土壤生態環境和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構成嚴重威脅。首先,土壤污染嚴重危害人體健康。土壤污染造成有害物質被農作物吸收,使有害物質通過食物鏈富集于人體內,引發各種急慢性疾病,危害人體健康。其次,土壤污染威脅生態安全。土壤污染直接影響土壤生態環境系統的結構和功能,導致依附于土壤的生物種群結構發生改變,生物多樣性減少。土壤污染還會導致水、大氣、海洋等環境要素的交叉污染,進而影響整個生態安全。最后,土壤污染影響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土壤污染使土壤生產力和耕地質量下降,導致糧食減產、糧食質量下降,進而影響整個社會的可持續發展。
二、我國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的缺陷分析。
土壤污染防治的法制化是我國根治土壤污染的基本路徑。
目前,我國涉及土壤污染防治的法律法規總體可分為環境保護基本法、土壤污染防治專門法及相關法三個部分。首先, 《環境保護法》 對土壤污染防治、農業環境保護作了原則性規定。
《環境保護法》 第 20 條要求各級人民政府對土壤污染和土壤生態環境破壞從水土整治、動植物保護、化學品及農藥安全等方面進行綜合系統防治。其次,我國目前尚無土壤污染防治的專門法律,現有與土壤污染防治密切相關的法律法規主要是 《水土保持法》 和 《土地復墾條例》。2007 年 《沈陽市污染場地環境治理及修復管理辦法 (試行)》 從監督管理、污染場地的評估與認定、污染場地的治理及修復、法律責任等方面對污染場地環境治理及修復管理進行了比較系統的規定。1995 年制定的《土壤環境質量標準》 對農田、蔬菜地、茶園、果園、牧場、林地、自然保護區等的土壤規定了不同的質量控制標準。最后,土壤污染防治相關法主要涉及 《大氣污染防治法》、 《水污染防治法》、 《固體廢棄物污染防治法》 等污染防治及 《土地管理法》、 《森林法》、 《草原法》、 《礦產資源法》 等自然資源保護方面的法律法規。另外,其他環境保護專門法中有助于土壤污染防治的還有 《環境影響評價法》、 《清潔生產促進法》、 《節約能源法》、 《農業法》、 《城市規劃法》、 《標準化法》、 《排污費征收使用管理條例》 等。
然而,我國土壤污染防治立法還相當不完善,存在嚴重的結構與功能缺陷,已明顯不能為防治土壤污染提供有力地法律制度保障。
第一,我國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的結構性缺陷。首先,立法缺乏系統性。涉及土壤污染防治的法律法規應是一個有機聯系的整體,而我國不僅環境保護基本法性質的 《環境保護法》 對土壤污染防治的規定相當簡單,而且還缺乏專門性的土壤污染防治單行法律法規。這既與當前嚴峻的土壤污染形勢極不相適應,也嚴重制約了土壤污染防治的工作開展。其他涉及土壤污染防治的法律法規只有關于土壤污染防治的零散規定,且這些規定多是宣言式和框架式的,既無對土壤污染防治的明確詳細規定,又缺乏相互配合聯系,無法為土壤污染防治提供有效的制度保障。其次,立法缺乏對土壤的統一性保護。現有土壤污染防治法律法規分別從不同的領域對不同的土壤進行規定,缺乏對土壤生態環境保護的基本化規定。立法的土壤規制對象比較狹窄,偏重規制農業土壤污染,對工業、城市土壤污染重視不足。再次,立法缺乏土壤污染防治的系統性制度供給。立法缺乏完善的土壤污染防治制度使得立法缺乏可操作性,行為規則原則性、概括性強,明確性不夠,缺乏針對性。最后,立法缺乏對土壤污染防治管理體制的系統性規定。我國的環境管理體制實行行政主管部門統一管理與各部門分工負責相結合管理。
目前,土壤污染防治行政主管部門不明確,行政主管部門與分工負責的各部門之間的職權劃分不清。環保、國土資源、水利、農業等部門多頭管理,無法有效應對復雜的土壤污染防治系統性工作。
第二,我國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的功能性缺陷。結構與功能具有對應關系,結構決定功能,我國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的結構性缺陷直接導致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的功能性缺陷。土壤污染防治立法在功能上是為了實現預防和治理土壤污染,而現有土壤污染防治立法存在明顯的重預防輕治理的結構性缺陷,其造成了土壤污染防治立法在治理土壤污染方面的功能性缺陷。即使在預防土壤污染方面,立法也存在嚴重的偏重控制點源污染,忽視對農藥、化肥、大氣污染、水污染等面源污染控制,導致土壤污染防治立法在防治土壤面源污染方面的功能性缺陷。在土壤污染治理上,立法更是很少涉及土壤污染治理,即使有土壤污染修復方面的地方立法,由于其立法層次低、適用范圍窄、手段單一,仍無法有效治理土壤污染。
三、域外土壤污染防治立法借鑒。
域外國家和地區對土壤污染防治主要實行專門立法、相關立法和綜合立法相結合的模式,實現了對土壤污染防治的系統性立法。
美國早在 20 世紀 30 年代就制定了專門的 《土壤保護法》,該法通過防治土壤污染、流失來保護農業生產。之后,美國又從對廢物全程管理的角度防治土壤污染,制定了 《固體廢物處理法》、 《資源保護回收法》、 《危險廢物設施所有者和運營人條例》、 《綜合環境污染響應、賠償和責任認定法案》、 《超級基金增補和再授權法案》 和 《納稅人減稅法》 等法律。此外,美國在水污染防治的 《清潔水法》、水源地保護的 《安全飲用水法》、化學品等有毒物質污染防治的 《有毒物質控制法》 和《聯邦殺蟲劑、殺菌劑和殺鼠劑法》 中從對各污染源的控制來加強土壤污染防治。
英國針對土壤污染防治制定了專門的 《環境保護 1990:
Part IIA法案》。另外,英國注重對污染的系統防治。 《污染控制法》 是英國環境保護的基本法,該法對廢棄物污染、水污染、空氣污染、噪聲污染等實行全面系統控制。英國還在對生活垃圾處理的 《生活環境舒適法》、對危險廢物控制的 《有毒廢物處置法》 和 《有毒污水處理法》 中從對各污染源的控制加強土壤污染的防治。
德國針對土壤污染制定了專門的 《聯邦土壤保護法》、《國土整治法》、 《聯邦土壤保護與污染地條例》 和 《建設條例》 等。“德國近期關于土壤污染防治的法律實踐主要包括法院的司法判例發展以及土壤污染防治政策的整合兩個方面。”
[4]同時,德國意識到僅僅依靠專門的 《聯邦土壤保護法》 等法律法規防治土壤污染是不夠的,需要將專門的土壤污染保護法律與涉及土壤領域的其他法律結合起來,實現土壤污染防治的專門化與系統化。德國先后制定 《循環經濟與廢物管理法》、《肥料和植物作物保護法》、 《基因工程法》、 《聯邦森林法》、《聯邦礦業法》、 《聯邦污染防治法》 等法律從不同領域實現對土壤污染的整體控制。
日本針對土壤污染防治也制定了專門的 《農用地土壤污染防止法》、 《土壤污染對策法》、 《土壤污染對策法施行規則》。
日本多次修訂 《農地土壤污染防治法》 并根據該法對農田土壤中鎘、銅、砷等含量進行監測,并對超標土壤予以修復。日本2002 年頒布的 《土壤污染對策法》 以市區的土壤污染為防治對象,對調查的地域范圍、超標地域的確定,以及治理措施、調查機構、支援體系、報告及監測制度等進行了詳細系統的規定。另外,日本在 《水質污濁防止法》、 《Dioxine 類物質對策特別措施法》 中也有涉及防治土壤污染的規定。
我國臺灣地區針對土壤污染制定了專門的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并制定了詳盡的配套法律規范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實施細則》、 《污染整治費收費辦法》、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的監測基準與管制標準》、 《征收種類與費率》 等共18 項法案,這些法案與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 相結合形成了臺灣地區比較完備的土壤污染防治立法體系。
四、系統完善我國土壤污染防治立法。
1.系統化完善我國土壤污染防治立法必要性。
系統化之所以成為我國完善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的目標,除源于我國防治土壤污染的迫切需要與對土壤生態環境的系統性認識加深,還源于人類環境保護理念的生態中心主義嬗變與系統論理論的發展。
首先,人類環境保護理念的生態中心主義嬗變要求立法實現對土壤污染的整體性防治。隨著人類對生態環境特性的認識加深,在深刻反思人類中心主義缺陷的同時,逐步確立起整體環境觀,并逐步形成一種全新的理念———生態中心主義來處理人類與自然的關系。生態中心主義要求生態系統中所有構成要素必須維護生態系統本身的相對穩定,堅持整體主義思想,實現生態系統本身的可持續發展[5]。生態中心主義強調整體性、內在聯系性,主張人與自然的統一,將生態系統的整體利益視為最高價值。環境法中的生態中心主義是指將人類和自然作為一個生態整體,從宏觀上指導環境立法、運行,規范人類行為的一種理念。土壤生態環境系統的整體性特點及土壤污染源的多樣化需要人類在土壤污染防治立法中樹立整體環境觀念,通過對土壤污染的多源整體性控制,實現土壤生態環境系統的可持續發展。
其次,系統論為系統化完善立法提供了理論基礎和具體方法。系統論是對系統科學的哲學抽象,強調整體性。所謂系統,是“由相互制約的各部分組成的具有一定功能的整體”[6]。系統論認為現實世界的任何事物都是以系統方式存在和運行的,系統具有多元性、層次性、相關性、整體性等特征,其總是動態運行并保持相對穩定。系統論在土壤生態環境保護中的具體運用是綜合生態系統管理,綜合生態系統管理在土壤污染防治立法中的具體運用是土壤污染系統控制,即對土壤污染進行“整體的、系統的、全過程的、多種環境介質的控制”[7]。一方面,土壤與水、大氣等環境要素共同組成完整的生態循環系統,因而,我國進行土壤污染防治還需加強對水、大氣等多環境介質的污染控制。另一方面,土壤生態環境系統在結構和功能上具有整體性,其各組成要素相互作用、普遍聯系而成為一個和諧的有機整體。土壤生態環境系統各組成要素在結構上具有層次性、組織性和有序性,在功能上相對獨立又密切聯系,共同維護土壤生態系統相對穩定的可持續發展。因此,完善的土壤污染防治立法必須遵從土壤生態環境的系統性規律,對土壤污染進行整體、全過程、多種環境介質的系統控制。
因此,我國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的系統化完善需要以生態中心主義理念為指導,強調土壤生態環境系統結構與功能的完整性,運用系統科學中系統論的方法,來實現對土壤污染的系統化防治。
2.系統化完善我國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的實現路徑。
土壤污染防治立法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需要對土壤生態環境系統進行系統化立法。系統化立法可以實現防治土壤污染、保護人體健康的目的,并最終實現土壤的可持續利用、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及保障土壤生態環境系統安全的目標。
(1) 修訂 《環境保護法》,實現對各環境介質的系統污染控制。隨著我國可持續發展戰略的實施、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建立與完善、政府職能的轉變、科學發展觀和社會主義生態文明建設理念的提出, 《環境保護法》 已嚴重不適應時代環境保護需求,亟需進行系統性修訂。“《環境保護法》 修改的最終目標乃是基本法和法典化。”[8]但我國現在還很難實現 《環境保護法》 法典化的目標,目前比較可行的途徑是先實現該法的基本法化。基本法化意味著 《環境保護法》 可以實現對環境的整體保護、對多污染源的系統控制。修訂后的 《環境保護法》
應明確以獨立章節規定保護土壤生態環境、防治土壤污染,引入綜合生態系統管理原則,建立適用于所有環境要素的保護與污染防治的法律制度,創立有效的對各環境要素的開發、保護與污染防治立法的協調機制。
(2) 制定專門的 《土壤污染防治法》 及配套法規、規章。
修訂后的 《環境保護法》 雖是環境保護、污染防治領域的基本法,但限于基本法性質制約,該法不可能對土壤污染防治做出詳細、具體的規定。針對土壤污染防治,我國還需制定專門的《土壤污染防治法》,實現對土壤污染的系統控制。
第一, 《土壤污染防治法》 在規定預防土壤污染的同時,偏重土壤污染治理與修復。土壤污染處于生態污染鏈的末端,目前已有大量立法對其他環境要素的污染防治進行了詳細規定, 《土壤污染防治法》 無需再將預防類單行法的污染防治內容分解納入。否則,不僅會造成立法資源的浪費,還會造成土壤污染防治立法與其他污染防治立法的重復。
第二, 《土壤污染防治法》 應堅持生態中心主義理念,樹立整體環境觀念,引入綜合生態系統管理原則。生態中心主義理念可以加深人類對土壤生態環境系統的認識,促進人類對土壤污染實現系統的污染控制。綜合生態系統管理原則是指在土壤污染防治中,從整個生態系統的角度綜合進行土壤污染控制,綜合考慮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和生態等各種因素,綜合采用多學科的知識和方法,綜合運用行政、市場和社會的調整機制,實現經濟、社會與土壤生態環境的可持續發展[7]。11~12 綜合生態系統管理原則是生態中心主義理念的法律化實現路徑,其直接催生土壤污染系統防治的具體法律制度。
第三, 《土壤污染防治法》 應系統規定土壤污染防治的各項制度。 《土壤污染防治法》 尤其要明確規定土壤保護規劃制度、土壤環境質量標準制度、土壤環境影響評價制度、土壤污染監測與鑒定制度、土壤污染法律責任制度、土壤污染修復制度、土壤污染防治基金和保險制度,實現對土壤污染的監測預防、使用管理、污染修復和損害賠償的全過程管理。另外,《土壤污染防治法》 可與在水、大氣等污染防治法中規定的排污許可制度建立鏈接,實行排污許可證的備案制度。
第四, 《土壤污染防治法》 建立統一的土壤污染監管體制。土壤污染監管體制是 《土壤污染防治法》 得到有效貫徹實施的支撐和中樞,是國家土壤污染防治戰略方針、政策、法律制度得以貫徹執行的保障。 《土壤污染防治法》 應明確中央土壤污染防治的主管部門,合理劃分土壤污染防治中央主管部門、地方分級管理部門和相關管理部門的職權,建立有效的各管理部門之間的溝通協調機制和嚴格的土壤污染防治問責機制。
第五, 《土壤污染防治法》 保障公眾參與土壤污染防治的權利。土壤污染信息公開是我國土壤法治的必然要求, 《土壤污染防治法》 應明確規定政府有責任主動及時公開土壤污染信息,保障公眾的知情權。 《土壤污染防治法》 應注意發揮社區和村委會在土壤污染防治中的作用,委托社區和村委會成員作為兼職監管員,以便及時掌握土壤污染信息。同時, 《土壤污染防治法》 應建立群眾監督、舉報土壤污染程序化回饋機制,保障公眾土壤污染參與權和監督權實現,給予百姓參與土壤污染防治門徑。
(3) 完善土壤環境質量標準體系,提高土壤環境質量標準。土壤環境質量標準是土壤環境法治建設的基礎,是土壤污染防治立法、執法、司法的依據。我國應“構建一個以 《土壤環境質量標準》 為基礎的,包含農用地土壤環保標準、場地土壤環保標準、土壤環境分析方法標準、土壤環境標準樣品和土壤環境基礎標準在內的較為完善的土壤環境標準體系。”同時,我國應不斷提高土壤環境質量標準,鼓勵地方政府制定嚴于《土壤環境質量標準》 的標準,以滿足各地不同的土壤保護需要。 《土壤環境質量標準》 應能對包括農村土壤和城市土壤的各類土壤規定嚴格的質量標準,應能全面綜合管理進入土壤的物質及物質留存土壤期間的狀況和離開土壤的狀況。
五、結論。
系統化的土壤污染防治立法是防治土壤污染的保障,可有效解決土壤污染防治原有立法的結構與功能缺陷。系統化之所以會成為我國完善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的目標,除源于我國防治土壤污染的迫切需要及對土壤生態環境的系統性認識的加深,還源于人類環境保護理念的生態中心主義嬗變與系統論理論的發展。人類秉持整體環境觀,使用綜合生態系統管理方法解決土壤污染問題,首先,應修訂 《環境保護法》,以獨立章節規定保護土壤生態環境、防治土壤污染,實現對各環境介質的系統污染控制。其次,應學習域外國家和地區的先進立法經驗,制定專門的 《土壤污染防治法》 及配套法規、規章。同時,我國在系統化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的同時,還要注意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系統的綜合協調,避免立法重疊, 《土壤污染防治法》 在規定預防土壤污染的同時,偏重土壤污染治理與修復。土壤污染防治法》 應系統規定土壤污染防治的各項制度,建立統一的土壤污染監管體制,保障公眾參與土壤污染防治的權利。第三,我國應完善土壤環境質量標準體系,提高土壤環境質量標準,尤其是鼓勵地方政府制定嚴于 《土壤環境質量標準》 的標準,以滿足各地不同的土壤保護需要。另外,水、大氣與固體廢物等環境要素的污染防治情況會嚴重影響土壤污染防治的效果,我國還要完善土壤污染防治相關立法,加強對其他環境要素的保護,完善水、大氣與固體廢物等污染防治立法,通過加強立法、嚴格執法、公平司法、引導守法,真正實現土壤污染的系統化防治。
【參考文獻】
[1] 楊志峰,劉靜玲。 環境科學概論(第二版) [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28)。
[2] 朱靜。 美、日土壤污染防治法律度對中國土壤立法的啟示 [J].環境科學與管理,2011(11):21.
[3] chinadialogue.net/article/show/single/ch/724,2012- 3- 9.
[4] 秦天寶。 德國土壤污染防治的法律與實踐 [J].環境保護,2007(10):70.
[5] GeorgeFrancis. EcosystemManagement,33 Nat [J].Resources J.,1993:315.
[6] 苗東升。 系統科學精要(第三版) [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20)。
第8篇:土壤環境特征范文
關鍵詞 污灌區;重金屬污染;潛在生態風險;評價;甘肅白銀;東大溝
中圖分類號 X53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7-5739(2015)15-0215-03
污水灌溉曾被認為是緩解農業水資源緊張狀況的重要途徑,但長期使用未經處理的污水進行灌溉,可能會導致污水中的重金屬等污染物在土壤中累積,并經過作物吸收進入食物鏈,或通過某些遷移進入地下水和大氣,最終威脅其他動物甚至人類的健康[1]。由于長期污灌已經引起了一系列的環境問題,如小麥拔節后抽穗少、蔬菜易腐爛不耐貯藏等[2]。因此,污染土壤修復技術已成為全球的熱點研究領域之一,通過土壤淋洗、加入土壤改良劑使重金屬固化或改變重金屬形態、微生物與植物的生物修復等措施,可以減輕或清除土壤的重金屬污染[3]。但無論采取何種污染修復技術,都必須先了解土壤污染狀況、污染類型和污染程度等,才能采取相應的措施。
白銀市位于甘肅省中部,黃河上游,地下水資源豐富,黃河流經市轄區,水能資源充足。面積2.12萬km2,人口180萬人。白銀地區礦產豐富,開采歷史悠久,礦產資源有銅、鉛、鋅、金、銀等金屬礦產及硫磺、煤炭、石膏、石灰石、芒硝、氟石等非金屬礦產。白銀市幾十年來粗放的有色金屬采選和冶煉加工,致使境內東大溝流域農田及周圍生態環境的重金屬污染問題嚴重,直接影響黃河流域生態安全。東大溝是白銀市東市區工業區的一條排污溝,起源于白銀公司露天礦,由北向南穿過白銀市東市區,流經38 km于四龍口匯入黃河。沿途主要接納了白銀公司、銀光公司等工業企業排放的工業廢水和東市區居民生活污水。作為農業灌溉用水的有效方式,東大溝沿線耕地用污水灌溉有很長的歷史。因此,研究污灌區土壤重金屬污染特征,對土壤環境質量進行評價,可為污灌區土壤重金屬污染修復提供科學依據。
1 研究方法
1.1 樣品采集
1.1.1 采樣區域與采樣點分布。本次研究基于2007年全國第二次土壤普查工作中在東大溝污灌6個不同區域(分別標記為A、B、C、D、E、F)采集的表層土壤,采樣深度為0~20 cm,共計50個,其中區域A有4個,區域B有10個,區域C有23個,區域D有3個,區域E有6個,區域F有4個,代表白銀市東大溝污灌區域土壤環境質量,采樣定位見圖1。
1.1.2 土樣采集與處理方法。測量重金屬的樣品用竹片或竹刀去除與金屬采樣器接觸的部分土壤,再用其取樣。等重量混勻后用四分法棄取,保留相當于風干土3 kg的土樣記錄裝袋。采樣結束后,采樣小組填好樣品流轉單,同樣品一起交樣品管理員。采集的土壤樣品放置于風干室的風干盤中,除去土壤中混雜的磚瓦石塊、石灰結核、根莖動植物殘體等,攤成2~3 cm的薄層,經常翻動。半干狀態時,用木棍壓碎或用2個木鏟搓碎土樣,置陰涼處自然風干。風干后的樣品倒在有機玻璃板上,用木錘敲打,用木棒再次壓碎,細小已斷的植物須根,采用靜電吸附的方法清除。混勻土樣,過孔徑2 mm的尼龍篩,去除2 mm以上的砂粒,大于2 mm的土團繼續研磨、過篩。過篩后的樣品全部置于無色聚乙烯薄膜上,充分攪拌、混合直至均勻,用四分法棄取、稱重,保留2份樣品,一份裝瓶備分析用,另一份繼續進行細磨,過孔徑0.15 mm的尼龍篩用于分析。
1.2 樣品分析
采用鹽酸-硝酸-氫氟酸-高氯酸全消解的方法,徹底破壞土壤中的礦物晶格,使試樣中的待測元素全部進入試液,使用Zeenit-700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計測定Cu、Pb、Zn、Cd,使用AFS-930原子熒光光度計測定As、Hg。所有測定均有空白樣和質控樣進行質量控制。
1.3 評價方法
污染評價的方法很多,目前使用較多的是指數法,不同的評價方法側重點不同。本次研究采用污染綜合指數法、污染分擔率對污灌區土壤重金屬污染特征進行評價,采用Hakanson潛在生態危害指數法對污灌區土壤生態風險進行評價。
1.3.1 土壤重金屬污染質量評價。土壤按照應用功能、保護目標和土壤主要性質劃分為3類,Ⅱ類主要適用于一般農田、蔬菜地、茶園、果園、牧場等土壤。土壤質量基本對植物和環境不造成危害和污染。本次評價區域執行《土壤環境質量標準》(GB15618―1995)Ⅱ類土壤標準[4],采用單項污染指數和綜合污染指數,對污灌區土壤重金屬污染進行評估。具體的數學模型如下。
單項污染指數:Pi=Ci/Si
污染分擔率:Ki(%)=(Pi/P)×100
式中,Pi為第i種污染物單項污染指數,Ci為第i種污染物的實測值,Si為第i種污染物的評價標準,P為污染綜合指數,Ki為第i項污染物所占的分擔率(%)。
土壤質量分級標準見表1。綜合污染指數全面反映了各污染物對土壤污染的不同程度,同時充分考慮了高濃度物質對土壤環境質量的影響。
根據國家土壤環境質量標準的定義,本文將土壤環境質量分為5個級別,具體分級見表2。
1.3.2 潛在生態風險評價。瑞典著名地球化學家Hakanson在1980年提出的潛在生態指數法(The Potential Ecological Risk Index)(RI)是一套應用沉積學原理評價重金屬污染和生態危害的方法。該方法作為國際上土壤(沉積物)中重金屬研究的先進方法之一,不僅反映了某一特定環境中不同污染物的影響,同時也反映了多種污染物的綜合影響,并定量劃分出潛在危害程度,是目前應用很廣的一種方法。我國著名學者陳靜生曾于1989年根據Hakanson的關于潛在生態危害指數評價方法介紹了6個重金屬元素的毒性系數的計算方法,并給出了毒性系數。隨后,我國眾多學者在研究土壤(沉積物)重金屬污染評價中也大量使用了潛在生態危害指數法。
單個元素污染系數:Cir=Ci實測/Cin
式中,Cir為某一種金屬的污染系數,Ci實測為土壤(沉積物)重金屬元素的實測含量,Cin為該元素的評價標準,某一重金屬的潛在生態危害系數Eir=Tir×Cir
某一點土壤(沉積物)多種重金屬綜合潛在生態危害指數:
Hakanson提出的重金屬毒性水平順序:Hg(40)>Cd(30)>As(10)>Pb(5)=Cu(5)>Zn(1),潛在生態風險指數可以定量評價單一元素的風險等級,也可以評價多個元素的總體風險等級。重金屬的潛在生態風險指標與分級關系見表3。
2 結果與分析
2.1 東大溝污灌區土壤重金屬污染特征
對白銀市東大溝污灌區50個點位表層采集的土壤樣品,使用原子吸收光度法和原子熒光光度法完成了6種元素(Cu、Pb、Zn、Cd、As、Hg)的測試。同時,選取全國第二次土壤普查中本地區環境土壤背景點的土壤樣品,并將此作為本地的背景值。監測分析結果可知,東大溝污灌區不同區域表層土壤中重金屬含量分布差別較大(表4)。由表4可知,6種重金屬含量均值大小在區域A、E、F中依次為Zn>Pb>Cu>As>Cd>Hg,區域B依次為Cu>Zn>Pb>As>Cd>Hg,區域C、D則為Zn>Cu>Pb>As>Cd>Hg。重金屬污染程度沿程分布呈現逐漸降低的趨勢。
以相關元素背景值為評價標準是土壤環境質量評價的最基本的依據之一,也是判別土壤污染程度與否的重要標準之一[5]。通過與白銀市土壤背景值比較,污灌區表層土壤中6種重金屬平均含量均顯著高于土壤背景值。其中,Cu的最高平均值達到土壤背景值的39倍(區域B),Pb為24倍(區域A),Zn為23倍(區域A),Cd為475倍(區域A),As為15倍(區域F),Hg為48倍(區域F)。除As和Hg外,其他重金屬元素的超標率為100%。因此,由于歷史原因和現實條件限值,常年使用處理未達標的污水灌溉,白銀市東大溝污灌區表層土壤已經出現了嚴重的重金屬累積現象,應引起農業環境部門的重視。
2.2 東大溝污灌區土壤重金屬污染質量評價
由于該地區的土壤pH均值為7.58,屬微堿性環境,故選擇國家土壤環境質量標準pH>7.5的二級限量值作為污染評價值,計算污灌區土壤中6種重金屬的單項污染指數值和綜合污染指數值,分析結果見表5。
從表5可以看出,根據單項污染指數法和綜合污染指數法的評價結果,污灌區表層土壤已經受到重金屬污染。在研究區中的重金屬,Cu、Pb、Zn、Cd、As、Hg的單項污染指數的變化范圍分別為1.06~7.57、0.50~1.99、0.73~4.46、10.7~62.0、1.68~6.92、0.14~1.89;單項污染指數均值分別為3.91、1.34、2.50、35.2、3.32、1.06,均大于1。在研究的污灌區中,Cd的污染指數最高,對環境的污染也最大。表層土壤重金屬的平均單項污染指數從大到小依次為Cd>Cu>As>Zn>Pb>Hg。
污灌區的綜合污染指數范圍為2.5~13.2,均值為7.9,污灌區土壤受到重污染,作物受到的污染已相當嚴重。由綜合污染指數看以看出,各個污灌區表層土壤重金屬污染程度為區域C>區域A>區域B>區域D>區域F>區域E。從分布的區域來看,重金屬污染程度呈現污灌土地沿流域自上而下,由近岸到遠離逐漸降低的趨勢。
污染物分擔率反映了各污染物在污染過程中所占的比率。從表6看以看出,污灌區表層土壤中6項污染物平均分擔率的順序為Cd>As>Cu>Zn>Pb>Hg,但不同區域中污染物分擔率有差別。在污灌區表層土壤中,Cd污染物分擔率明顯高于其他污染物,平均值達到了72.51%,因此東大溝污灌區表層土壤重金屬的污染程度主要由該地區Cd的污染程度來判定。從污染因子結構來看,與東大溝納入廢水企業明顯相關。
2.3 東大溝污灌區表層土壤潛在生態風險評價
根據東大溝流域特點,綜合本地區背景土壤不會對東大溝污灌區土壤中重金屬含量造成影響情況,本次研究確定以《土壤環境質量標準》(GB15618―1995)Ⅱ類標準進行生態風險評價。
表7列出了白銀市東大溝污灌區表層土壤單個重金屬潛在生態風險系數和綜合生態風險指數。通過計算結果可以看出,污灌區表層土壤重金屬綜合潛在生態危害指數為352~2 009,平均達1 159,生態風險達到很強生態風險,只在區域E(RI=352)為較強生態風險,表明白銀市東大溝污灌區表層土壤受到嚴重污染,應引起充分的關注。污灌區表層土壤6種重金屬的潛在生態風險系數Eir范圍:Cu為5~38,Pb為3~10,Zn為1~4,Cd為321~1 860,As為17~69,Hg為6~76。從6種重金屬的潛在生態風險系數的均值來看,其潛在生態風險程度為Eir(Cd)>Eir(Hg)>Eir(As)>Eir(Cu)>Eir(Pb)>Eir(Zn)。在整個污灌區表層土壤中,Cu、Pb、Zn處于輕度的潛在生態風險,而Cd則處于極強的潛在生態風險。As在區域F中處于中等的潛在生態風險,在其他區域則處于輕度的潛在生態風險。Hg在區域B、C、F中處于中等的潛在生態風險,而在其他區域處于輕度的潛在生態風險。由此可見重金屬Cd為東大溝污灌區表層土壤重金屬污染首要污染物。表7分析結果表明,污灌區表層土壤中處于很強的潛在生態風險水平,則主要是由Cd所引起的。Cd的潛在生態風險系數均值為1 055,遠高于極強生態風險值,在6個區域50個點位中,僅有1個點位為中等生態風險水平,占所監測點位的2%;3個點位處于較強生態風險水平,占所監測點位的6%;7個點位為很強生態風險水平,占所監測點位的14%;其余的39個點位達到極強生態風險水平,占所監測點位的78%[6]。
第9篇:土壤環境特征范文
關鍵詞 農村;環境質量;現狀;指標體系;江蘇泰州
中圖分類號 X82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7-5739(2016)01-0231-02
Rural Environmental Quality Evaluation of Taizhou City
HE Juan ZHAO Li
(Taizhou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Center of Jiangsu Province,Taizhou Jiangsu 225300)
Abstract The rural environmental quality index was employed to evaluate the quality of rural environment,and to classify the level of evaluation results. The index of the rural environmental quality evaluation by field study was analyzed,and taking the Heheng Village,Jishi Village of Taizhou City for example to test the system.
Key words rural area;environmental quality;status;index system;Taizhou Jiangsu
近年來,環境污染有加重的趨勢,但我國目前主要在城市環境保護中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對農村環境保護關注較少[1-2],相關的研究和評價剛剛起步[3]。一方面,農村環境污染具有排放主體分散性、隨機性、不確定性等特征;另一方面,目前的環境監測和評價方法主要是針對城市環境而設立的,不適合應用于農村環境評價監測,如何改進環境監測和評價標準,是目前農村環境保護的重中之重。
1 農村環境質量概述
農村環境的種類與城市環境不同,最主要的特點是功能分區不明顯,也完全區別于農業環境,它更加側重于人類的生活環境[4]。在這里提到的農村環境質量是指農村的土壤、空氣、水等自然資源的環境質量,同時也包括在這種環境中生產的農林牧副魚等農產品的質量,即與農村人口居住和生產生活密切相關的環境質量。
目前,農村環境質量監測滯后于農村的發展,許多監測項目不適合農村環境,農村環境中污染較嚴重的項目監測有些還存在缺失,而不嚴重的污染項目存在重復監測的情況[5]。
同時由于農村環境質量監測剛剛起步,研究者僅僅初步構建相關的監測和評價方法,有許多方面需要改進,并且尚需投入大量的精力進行指標的細化,以真實地反映農村人居環境和農村環境質量現狀。
2 農村環境質量評價方法的建立
2.1 指標體系的建立
根據完整性原則、代表性原則、可操作性原則,以及對泰州市典型農村地區基本情況的調查,包括社會經濟與自然概況、農業生產情況、水源地情況以及污染狀況等,確定了泰州市典型地區的農村環境質量的評價指標體系。指標體系由高到低分為“目標層”“準則層”“指標層”3層,指標層共計10個指標(表1)。
2.2 農村環境質量評價方法
農村環境質量綜合指數計算方法公式如下:
RQI=Cenv×Ienv+Ceco×Ieco(1)
式(1)中,RQI為農村環境質量綜合指數;Cenv為農村環境狀況指數權重,為0.6;Ienv為農村環境狀況指標值;Ceco為農村生態狀況指數權重,為0.4;Ieco為農村生態狀況指標值。
各指標層因子解釋如下:
2.2.1 地表水環境質量指數。以《地表水環境質量標準》(GB3838―2002)為評價依據,評價采用單因子標準指數法,根據水質類別確定地表水水質指數:Ⅰ類對應指數100,Ⅱ類為90,Ⅲ類為80,Ⅳ類為40,Ⅴ類為20,劣Ⅴ類為0。
2.2.2 飲用水源地水質指數。選擇主要水源地開展監測評價。以《地表水環境質量標準》(GB3838―2002)Ⅲ類為評價依據,評價采用單因子標準指數法,根據水質類別確定地表水水質指數:Ⅰ類對應指數100,Ⅱ類為90,Ⅲ類為80,Ⅳ類為40,Ⅴ類為20,劣Ⅴ類為0。
2.2.3 環境空氣質量指數。根據公式計算:
環境空氣質量指數=100×(1-A/N)(2)
式(2)中,根據《環境空氣質量標準》(GB3096―2012)二級標準評價,A為1 h平均值超標個數;N為各點位的監測數據個數總和。
2.2.4 環境狀況指標。由地表水環境質量指數、飲用水源地水質指數、環境空氣質量指數、理化指標土壤環境質量指數、有機指標土壤環境質量指數、生活污水處理設施出水水質指數加權組成。各指標權重分別為0.20、0.20、0.25、0.20、0.15。
2.2.5 土壤環境質量評價。采用單項污染指數法。計算公式:
Pip=Ci/Sip(3)
式(3)中:Pip為土壤中污染物i的單項污染指數,Ci為土壤中污染物i的實測濃度,Sip為污染物i的評價標準。根據Pip值的大小,將土壤污染程度劃分為5級,評價分級標準見表2。
2.2.6 生態環境狀況指數。根據《農村環境質量綜合評價技術規定》(試行)中的評價方法,農村生態狀況指數Ieco由生物豐度指數、植被覆蓋指數、水網密度指數、土地退化指數、人類干擾指數加權組成。各指標權重如下:生物豐度指數0.20,植被覆蓋指數0.20,水網密度指數0.20,土地退化指數0.15,人類干擾指數0.15。
2.2.7 農村環境質量綜合評價。根據農村環境質量指數大小,將農村環境質量分為5級,即優、良、一般、較差、差(表3)。
3 泰州市農村環境質量狀況監測與評價
3.1 典型村莊的選擇
季市村位于靖江市季市鎮中心,河橫村位于姜堰區沈高鎮,分別位于泰州市南部地區、中部地區。其中季市村占地8.8萬m2,總人口1 328人,歷史文化悠久,村內有始建于明代洪武5年,距今有640年以上歷史的青龍寺,有蘇中地區第1尊“藥師佛”,村中環境優美。該村對泰州地區農村生態環境研究具有典型性,其生活方式得到了國內外環境保護機構的認可,并且該村通過發展生態觀光農業,促進了該村的經濟發展的同時保護了環境。
3.2 監測結果
3.2.1 飲用水源地質量監測結果。對泰州市三水廠、靖江市三水廠進行監測,其監測結果通過單因子評價法,進行評價分析,評價分析的標準是依據國標GB3838―2002《地表水環境質量標準》Ⅲ類標準為依據。結果表明,《地表水環境質量標準》(GB3838―2002)中27項指標,總氮項目不計入評價,該水源地的水質指數到達80,符合國建地表水環境質量標準的Ⅲ類標準。
3.2.2 地表水環境質量監測結果及評價。對靖江市上青龍港、下青龍港口,姜堰區林場公路橋、洪林大橋進行了地表水環境質量監測,監測的項目依據國標GB3838―2002《地表水環境質量標準》中規定的基本項目24項,地表水各項監測指標均達到《地表水環境質量標準》的Ⅲ類標準,水質評價為良好,地表水水質指數為80。
3.2.3 環境空氣質量監測結果及評價。對季市村、河橫村的環境空氣進行了監測,所測指標PM10、二氧化硫、二氧化氮的濃度值都要優于國標《環境空氣質量標準》(GB3096―2012)規定的環境空氣質量二級標準,環境空氣質量指數為100。
3.2.4 土壤監測結果及評價。姜堰區河橫村選擇了3個基本農田監測點位,1個草莓園監測點位、1個葡萄園監測點位,靖江市季市村選擇了1個基本農田,1個種植園,1個商住區,共計8個監測點位。進行土壤環境質量監測的相關指標都優于國標《土壤環境質量標準》(GB15618―1995)所規定的土壤環境質量二級標準,土壤環境質量指數為100。
根據上述方法進行計算,河橫村、季市村的環境狀況指數均為92.0。
3.2.5 生態環境狀況監測結果。根據Landsat8 TM衛星遙感影像解譯結果顯示,泰州生態環境狀況指數為65.15。
3.3 評價結果
對泰州市的農村進行了農村環境質量評價,泰州市靖江市季市村和姜堰區沈高鎮河橫村的農村環境質量指數均為81.3,按照農村環境質量分級評價標準,評價的結果都為良。
4 結語
河橫村、季市村均是以農田種植為主,正在發展特色農業和生態旅游。環境質量評價結果說明,農村環境處于良好級別,屬于輕微污染,生態環境良好,基本適合農村居民生活和生產。評價結果與現實情況基本符合。
農村環境污染具有排放主體分散性、隨機性、不確定性等特征,并且農村環境功能分區不明確等特點,進行農村環境質量指數構建時,使用農村生態環境質量狀況、空氣質量、地表水土壤環境質量等作為分項指數,其在指數中所賦權重是否恰當,尚需進一步驗證。
目前,農村環境質量評價相關研究欠缺,目前的監測和評價方法亟待改進,這也為環境監測工作者提出了問題和挑戰,需要在未來投入大量的精力進行研究。
5 參考文獻
[1] 易國鋒.我國農村環境保護的困境及對策[J].環境管理,2007(6):80-83.
[2] 于水斌.農村污染方資格證已迫在眉睫[J].四川環境,2007,26(1):112-114.
[3] 朱承聿,單正葡.基層環境監測站開展農村生態環境質量監測與評價的探討[J].中國環境監測,1994,10(5):41-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