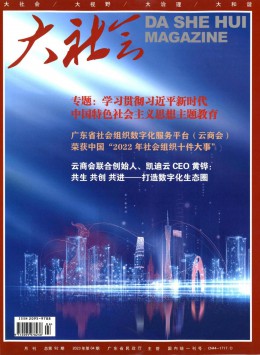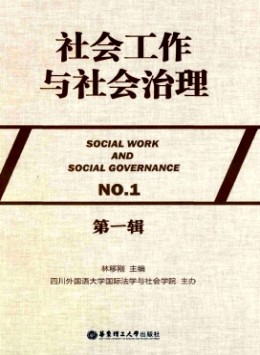社會記憶理論下的檔案與城市文化建設
前言:想要寫出一篇引人入勝的文章?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社會記憶理論下的檔案與城市文化建設范文,希望能給你帶來靈感和參考,敬請閱讀。

摘要:在社會記憶理論下,一座城市的檔案記錄著城市的歷史,引領人們回望城市的起源、發展,凝聚市民的身份感和認同感,并以此展望城市的未來。本文探討社會記憶理論視角下,檔案在城市文化建設過程中所起到的作用及實現機制,并對如何更大程度地發揮檔案價值做出研究。
關鍵詞:社會記憶;城市記憶;檔案記憶觀;檔案
一、社會記憶理論下的城市文化內涵
自哈布瓦赫提出“集體記憶”[1]的概念以來,唐納頓和哈拉爾德•韋爾策等學者對該概念進一步發展和演化,逐漸形成“社會記憶”理論,為歷史學、民族學、人類學、社會學等學科開辟了新的研究方向。在此背景下,檔案學引入“社會記憶”理論的核心概念,提出“檔案記憶觀”[2],認為檔案是社會記憶的載體,是社會記憶的物化形態,是建構社會記憶的重要資源,也是控制社會記憶的工具。城市文化是城市一切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成果總和,承載著市民對城市的認知和情感,并以此凝聚市民的身份認同。城市文化由所有市民共同書寫,同時以其特有的精神和氣質反作用于市民的思想和精神,并隨歷史的發展不斷傳承。
二、檔案參與構建城市文化的機制
(一)以記錄歷史,回溯城市文化發展檔案是對歷史的原始記錄,一座城市的檔案機構是城市集中保存記憶的場所。檔案中記錄的城市從古至今的重大事件、著名人物、經濟建設、城市規劃、主要建筑、節慶民俗,都是城市文化的形成基礎,回答了城市由何而來、如何而建、有何故事。不同的歷史,賦予不同城市各自獨特的文化特征,也使城市具有與眾不同的精神氣質。人們以檔案為渠道,探知城市自身的歷史和風貌,從而能夠了解自己城市的文化根基,并通過對檔案的不斷挖掘,使城市文化不斷深化。檔案所記錄的歷史,不僅反映了城市文化的源頭,更讓城市文化具有了更深刻、更厚重的底蘊,能培養市民的榮譽感和自豪感,從而建立身份認同,實現對城市及城市文化的歸屬。
(二)以收集鑒定,拓展城市文化邊界時代的進步變遷和城市的發展建設,都使新的檔案不斷誕生,這些新的檔案反映了新時代獨有的風貌,記載著城市新的記憶。對于城市文化而言,檔案機構對這些新生成的檔案進行收集、鑒定和整理,確定其歸檔范圍、判斷價值并確定保管期限,是一個決定了什么樣的城市文化能夠保存下來并留存后世的選擇過程,反映了城市的價值判斷和取向。新收集歸檔的檔案,一方面是對歷史的連續記錄,是城市文化延續發展的基礎;另一方面,也是將新的文化因素引入原有城市文化,不斷拓展城市文化范圍和邊界。優秀的傳統文化和新生的時代文化,共同使城市文化實現延續性與動態性的結合,使之更具生命力。
(三)以教育宣傳,啟發城市文化未來城市文化由公眾共同創造而成,承載著從過去到現在的記憶與情感。檔案是這種記憶與情感傳承與傳播的物質載體,在時間上,檔案將歷史記錄下來,完成代際傳承;在空間上,檔案將原本僅存在部分市民中的信息,經由歸檔與信息公開,向城市全體傳播。因此,檔案成為不可替代的公共教育資源。在西方國家,公共檔案館逐漸承擔起公眾教育職能,開發相關資源,為公眾提供歷史教育和文化教育,開展檔案宣傳,使公眾獲得身份感、認同感,認識到自身與所處地方的緊密聯系,不斷提高公眾文化素質[3]。城市未來的文化,也由市民繼續書寫,在市民文化水平提高的前提下,城市文化也將在延續已有文化的同時,獲得更加高質量的發展與繁榮。
三、提升檔案在城市文化建設中價值的策略
(一)增強檔案資源建設,擴展檔案收集渠道建設豐富的檔案資源,是一切檔案工作開展的前提。但是,檔案資源的收集過程,永遠是有選擇性的。傳統上,檔案機構多傾向從政府的角度出發,主要留存官方的敘述,而較少地將普通民眾、社會中的個人納入檔案保存。社會記憶理論為檔案文化和城市文化研究開辟了新的研究視野,把權力、利益、情感、社會情境、群體力量等諸多社會要素引入到檔案學中來[4],讓我們進一步思考檔案的價值和意義。從社會記憶的角度出發,讓檔案參與城市文化的建構,檔案工作者首先需要考慮什么樣的檔案,能夠最真實、客觀、全面地反映城市文化,不僅要保存“自上而下”的政府文書、官方記錄,也要留存“自下而上”的市民聲音,使二者共同成為城市文化的形成來源。檔案機構除了被動等待政府、社會組織等歸檔外,也應采取主動收集的方式,尋求有價值的原始記錄加以歸檔,并注意甄別其真實性,如結合口述歷史等歷史研究新方式,多角度地匯集和整合城市記憶。在檔案載體形式上,也不局限于傳統的文書檔案,圖像、聲音、視頻、數字網絡多媒體信息等新的載體形式正日益涌現,檔案機構也應與時俱進,讓城市文化得以多樣化保存,并使之呈現更為現代化、生動化的特征。在大數據時代,檔案機構還可以對城市系統運行狀態和歷史數據進行全面采集與整合,開發面向智慧城市建設需求的新型城市記憶工程[5]。
(二)運用新技術,探索教育宣傳渠道過去的檔案機構,更多重視檔案保存與保護,而較少參加到文化建設中。在城市文化的視野中,通常處于較為沉寂的位置。因此,在市民的認知里,檔案機構經常被忽視,限制了檔案價值的發揮。隨著時代的發展,檔案工作者的意識也在逐漸發生轉變,開始參與到文化建設中來,通過實踐,逐漸探索以檔案參與城市文化建設。檔案機構可以通過舉辦展覽的方式,向市民公布文化信息,吸引市民前來參觀,提升市民的知識水平和文化水平;也可以利用自身優勢,編纂、出版有關城市歷史、市民生活、市井風俗、街道建筑等與城市文化相關的檔案編研產品,從市民喜聞樂見的角度出發,提升城市文化內涵,喚起市民的文化記憶,引發市民情感認同。應鼓勵檔案機構采用網絡、新媒體等渠道,進駐流行的社交媒體如微博、微信公眾平臺等,制作圖文、視頻等文化宣傳信息,使檔案和檔案機構更頻繁地走進市民的視線,潛移默化地向市民傳達城市的歷史與記憶,拉近檔案與公眾的距離。檔案機構也可與當地的中小學、高等院校合作,采取線上線下相結合的方式,在學生中開設城市文化相關課程或講座,參與鄉土課程教材編寫等,在青少年群體中,樹立檔案意識和市民意識,以城市文化感染和熏陶未來的城市建設者,讓城市文化得到良性的可持續發展。
參考文獻:
[1]莫里斯•哈布瓦赫.論集體記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2]丁華東.檔案記憶觀的興起及其理論影響[J].檔案管理,2009(1):16-20.
[3]譚必勇.如何拉近檔案館與公眾的距離——解讀西方公共檔案館公眾教育職能的演變[J].圖書情報知識,2013(4):85-94.
[4]丁華東,崔明.“城市記憶工程”:檔案部門傳承與建構社會記憶的亮點工程[J].檔案學研究,2010(1):40-45.
[5]趙生輝,朱學芳.“城市記憶工程2.0”理論與實踐初探[J].圖書情報知識,2014(5):30-38.
作者:馬云娜 單位:遼寧師范大學檔案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