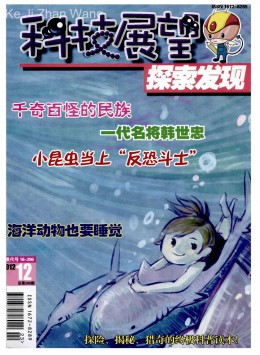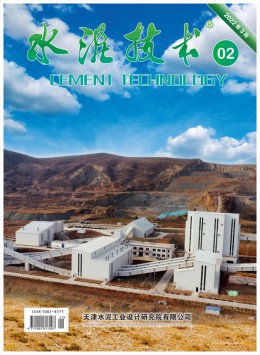二年級語文論文精選(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誕生,需要你不斷地搜集資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編為你收集了豐富的二年級語文論文主題范文,僅供參考,歡迎閱讀并收藏。
第1篇:二年級語文論文范文
2012年11月28日上午,由《中國攝影家》雜志和包商銀行聯合主辦的《文明與遺產—第二屆“包商銀行杯”中國國際攝影雙年展·世界遺產攝影論壇》在中國藝術研究院成功舉辦。
論壇上,“我們的家園·世界遺產”圖片社總監杰夫·史蒂文先生發表了題為“如何通過攝影完整呈現世界遺產”的演講,通過介紹他在埃及金字塔、古巴特立尼達山谷、日本廣島原子彈爆炸和平紀念碑、伊朗伊思法汗王侯廣場、韓國歷史村落和英國威斯敏斯特議會大廈等世界遺產地的拍攝經歷,闡述真實記錄世界遺產的重要性以及“我們的家園·世界遺產”團隊是如何拍攝并完整呈現世界遺產的。
論壇由《中國攝影家》雜志執行副主編張惠賓主持,與會嘉賓各抒己見,從不同角度闡述如何完整記錄世界遺產,創作出真實性與藝術性俱佳的攝影作品,并就中外在拍攝世界遺產時存在的攝影觀念,攝影視角的差異進行討論,探索今后世界遺產攝影的發展方向。以下為論壇講話摘錄。
張惠賓:歡迎來到今天的論壇。首先介紹一下今天到會的嘉賓和朋友:第一屆、第二屆中國國際攝影雙年展策展人黛安娜·金斯博瑞,中國藝術研究院攝影藝術研究所所長、《中國攝影家》雜志主編李樹峰,《中國攝影家》雜志社副社長劉偉,北京印刷學院設計藝術學院副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史民峰,北京電影學院攝影學院唐東平教授和鄭濤老師,《文藝研究》造型藝術編輯室主任金寧,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數字化保護中心主任丁巖,攝影師李少白、譚明、李建惠、楊樹田,以及來自北京電影學院和北京印刷學院的同學們,歡迎大家!
下面由來自新西蘭的藝術家杰夫·史蒂文作題為《如何通過攝影完整地呈現世界遺產》的演講。史蒂文先生是新西蘭知名攝影師、電影導演和電影制片人,他的攝影作品曾在澳大利亞、亞洲、歐洲和美國展出,并舉辦攝影作品展。同時,史蒂文先生還是“我們的家園·世界遺產”圖片社的總監,對于世界文化遺產的拍攝,在理念和拍攝技術上他都有著自己的體會,他也非常愿意和大家進行交流。
史蒂文:感謝大家,感謝有這么多對攝影有興趣的朋友來這里聽我談談世界遺產的拍攝。
我先概括地講一下今天我想要演講的這個主題。世界遺產是列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名錄的一些遺址,同時它也是全球對人類有重要意義的一些地方。全世界已經有190多個國家簽署了保護世界遺址名錄,中國當然也是其中之一。目前,世界上有962處文化遺址列入了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名錄》中,“我們的家園·世界遺產”圖片社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有合作關系,幫助他們對這些遺址進行拍攝,作為記錄和教學使用。目前,我們已經準備了300多幅照片,涉及90多個國家,我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之所以選取“我們的家園”這樣一個主題作為公司的名稱,包含兩層含義。首先是用“我們”二字表達了一種責任感,既然這些遺產是我們的,那我們有責任去善待它、保護它;第二部分—“家園”。“家園”是非常熟悉親切的,我們對它會有特殊的感情,所以“我們的家園”就是暗含了這樣一種意思:它是我們的財產,我們有責任去愛護它、保護它,這也是我們人類一種共同的心聲。
為什么要攝影世界遺產?攝影是容易被大家理解的一種傳播方式,它是無國界的,世界各國人民都可以通過圖片來認識和了解攝影人想表達的內容。攝影所具備的這種才能,決定了可以通過攝影這種超越國界的、超越文化的形式,將不同文化、不同國家的世界遺產展示給世界上每一個人。對攝影師而言,他們的挑戰不僅是在某處遺產拍出一幅好的作品,而是去拍攝不同的世界文化遺產,完成100多幅能全面展示遺產的照片,他們身上擔負著很重大的責任。
在這里,我展示的作品,它們或許并不是世界上最好的圖片,也不是帶有藝術性的藝術攝影,但是它們很真實的記錄了世界文化遺產原貌。我也希望大家在看到這些照片后,能開啟你們自己的一段想象力之旅。
現場聽眾:您好!我想提一個問題,我是很喜歡拍世界文化遺產的中國攝影師,我想問您,您在拍世界文化遺產的時候,在表現這些畫面的時候,您認為藝術性更重要呢,還是介紹性重要?或者說您在什么時候更能夠表現它的藝術性,在什么時候能夠更顯示它的介紹的作用?
史蒂文:我覺得在拍攝世界遺產的時候,藝術性是要兼顧的,但是不能讓它超越了介紹這處遺產本身的這種功能。因為作為我們這個拍攝世界遺產的攝影師團隊,不希望過于表現屬于自己的個人風格,而是攝影師能以一種統一的,真實而理性的態度去拍攝,而不是在拍攝過程中非常彰顯個人風格。另外,我們不建議通過Photoshop這種現代修片的手來處理世界遺產的圖片,還是要注重圖片的真實性和客觀性。
楊樹田:我拍了很多年的中國的世界遺產。在剛才展示的一些作品里,我感覺,拍攝世界遺產還是應該充分利用攝影語言,尤其是攝影的一些表現手法。比如那張羅馬斗獸場的照片,我感覺,在視覺表現和拍攝手法上,還不是非常到位。換作我,可能就不會那么拍。另外,在拍攝世界文化遺產的時候,重視作品的介紹性,我覺得也應該要有藝術性。畢竟遺產攝影也是視覺藝術,在表現它的同時,要把它的獨特性,通過表現手法突出出來。
史蒂文:羅馬斗獸場,只是羅馬眾多的世界遺產建筑之一。我覺得不是每一處都需要用藝術的手法去表現,可能通過這種非常簡單的、直接的這種記錄的功能去表現它會更好,而有的照片可能需要藝術性更多一點的技巧。另外,對于攝影家來說,可能是每一處遺產都拍了一個系列,但從中挑出最好的一張,最有代表性的一張是有難度的。
楊樹田:是這樣的。但是在介紹遺產的同時,還是應該突出遺產攝影視覺表現的藝術性,不能就是單一的純的記錄。
史蒂文:作為一名好的攝影師,可能沒有一個統一的標準去評判什么是一幅好的作品。攝影師應該是在記錄它的同時,讓它的美自然地呈現出來,而不是憑借自己主觀的去想把它拍得美。因為有一些本身就是非常美的風景,拍攝它,不管怎么樣拍,它都很美,它客觀上就是一件很美的事物,所以不用刻意的去營造。我們攝影師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也是一個信使,是要傳達客觀的真實,傳達某種信息。我認為這些自然的遺址或者自然風景本身就是一件藝術品。
楊樹田:中國攝影家在表現世界遺產的作品中,也很少用Photoshop進行后期處理,基本上都是原汁原味的呈現。
唐東平:剛才史蒂文先生預示了一個觀點:拍攝遺產的作品盡可能不要以追求美為主,而這引發了一些爭論。那么我們特別想知道,拍攝此類作品是不是有一個比較成型的行規。攝影要規避主觀幾乎是不可能的。我個人是這樣理解史蒂文先生的講話:史蒂文先生好像也不反對美,不反對把遺產拍得更美。不要刻意去求美,但如果是你“意外”獲得的美還是值得肯定的,只要后期不做任何的修改就好。這就又與他前面提到的“對美要有控制的,要有節制的,不要一味的去追求美”這樣一個標準有些混亂。
因此,我特別想知道,作為國際上的遺產拍攝的一些操作規程。因為我們發現,我們國內的創作與國際上是不一樣的,有差異,我們想向國際上比較先進的創作理念學習。想請史蒂文先生給我們介紹一下,用概括的話給我們描繪一下他們的理念或者說是一些標準體系。
史蒂文:作為攝影師來說,這是非常好的一個問題,我們也一直在探索,怎么去平衡我們所看到的和想到的。我們沒有一個非常固定的標準。我和我團隊目前的原則是,可以有創造性的去拍攝這些場景,發揮他們的自己創造性,但是要為這些遺產服務。他們的標準角度就是通過攝影師的眼睛,讓大家能感覺到為什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會選取這樣一處遺址成為世界文化遺產。
有的攝影師,去羅馬可能會拍一些非常漂亮的藝術照,或者為這些景觀拍攝廣告,這樣出發的角度是不同的。而對于他們這樣的攝影師來說,就是拍攝世界遺產,他們是持一種中立的態度。而且有某種協議的約定,讓他們很真實的去記錄,當然這也不乏其中個人的一些創作性的因素,可以發揮很多自己的創造性,自己的見解,但不能太突出自己的風格,還要保持一種中立的態度。
孫志遠:大家好!我叫孫志遠,是一個視障人,目前我正在致力于視障人攝影,就是利用視覺以外,比如說聽覺、嗅覺,還有其他感官參與創作拍攝的探索、推廣和培訓。我想問一個問題,是關于它的創作當中,如何運用動與靜的這個關系。世界遺產本身是一個靜態的東西,但是我看到他的作品當運用了很多動的元素,比如光、水、人等。那么在他的創作過程中,怎么將這些動與靜的元素進行結合,怎么取舍,怎么判斷?
史蒂文:我覺得作為攝影師,到了世界遺產的所在地,要集中自己的情感,調動視覺、聽覺、感知各方面的能力,將各種體驗、體會于一身,把要拍攝的文化精髓要抓住。有時候,如果我們足夠幸運的話,一張照片就能夠反映出整個遺產的全貌。但在通常情況下,到了某一處地方,我們都會充滿各種各樣感情,也不可能僅僅通過一張照片就呈現出所有想表現的東西。
史蒂文:攝影師還有一個職責,有時候為了追求美的視覺呈現,可能要規避一些影響構圖的事物。發現一處非常完美的地方非常難,美到沒有任何瑕疵,這是不可能的。我會調用現場條件,去遮蓋或者規避不必要的元素,這樣可以更好的呈現后面這處遺產景觀。當然,如果用Photoshop的話會很容易去掉這些不必要的元素,但是用Photoshop的話就缺少了它的真實性、客觀性。我們不太愿意用這個方法,而是選擇通過角度去遮蓋。
在伊斯坦布爾拍攝時,那里有非常多的鳥,有時候這些鳥會影響拍攝,但我們可不可以將鳥作為拍攝的元素之一呢?
李樹峰:首先,我想跟大家先介紹一下我們為什么要舉辦這次“世界遺產攝影論壇”。中國藝術研究院攝影藝術研究所與《中國攝影家》雜志,一直致力于攝影學術的研究,中國國際攝影雙年展正是我們的一個常規項目。
去年舉辦的第一屆中國國際攝影雙年展以“百姓·百年”為主題,把全世界各地的,關于中國160年來的老照片都征集、匯總了一下。展覽匯集關于中國人百年社會生活的視覺記憶,在攝影和人類生活記憶之間建立起了一種內在聯系。而今年的雙年展則是以“文明與遺產”為主題。我們想通過這個展覽和今天的論壇,在中國攝影業界進一步強化“遺產攝影”這個概念,把“遺產攝影”從風光攝影、廣告攝影、旅行攝影里邊給它強化、提煉出來,讓我們更加清楚地認識什么是遺產攝影,遺產攝影跟其他攝影有什么不同,有什么特殊的要求。本屆雙年展展出了380幅照片,在展覽現場,你可以更加強烈的感覺到遺產攝影與其他攝影的相同和不同之處。
中國所擁有的世界遺產相當多,拍攝世界遺產的人也很多。我們在座的攝影家,比如譚明老師、李少白老師、楊樹田老師以及李建惠老師、唐東平老師,都涉及到世界遺產的拍攝。遺產拍攝到底有哪些要求?遺產攝影與旅行攝影、風光攝影有哪些相同和不同之處?我們希望在座的同學們,有志于遺產攝影研究的同學,在前人努力的基礎上,好好思考一下這個問題。
在“遺產攝影”中,剛才大家都提到一個在真和美之間,在說明性和詩性之間如何平衡的問題。攝影的說明性,就是剛才李建惠老師用到的“介紹性”。在“遺產攝影”這個概念的框架下,攝影人在具體拍攝的時候,如何去把握、運用攝影方法與技巧,既突出遺產本身的特點,又發揮攝影的藝術性,增強作品的感染力和吸引力,這個需要好好動一番腦筋。
我相信,咱們中國的遺產攝影,會走向一個新的一個階段。我特別渴望中國的遺產攝影能夠形成一個強大的攝影家的陣容,同時也希望在我們大家共同的努力下,逐步建立一個具有專業標準和專業水平,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所認可的系統的遺產圖片庫。這對于我們整個人類文化遺產宣傳是一個很好的推進。
我們中國藝術研究院有“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中心”,其實自然遺產、文化遺產、自然與文化復合藝術和非物質文化遺產之間都有很強的聯系,有一些共同點。我們現在要著力研究這些遺產的共同點,遺產為什么重要?從不同的角度我們可以給它下不同的定義,但是有一些基本的意識我們需要明確:遺產是人類文化的活化石,遺產是人類文明的基因圖譜。看不同國家、不同民族留下來的遺產,我們能夠發現和尋找到一條人類文明發展演化的路線圖。遺產的重要性就在這里,它的偉大光輝之點也在這個地方。正如黛安娜在策展前言里邊說到的,我們不看過去的這個地圖,文明的地圖,就不知道我們今后往哪里走。
其實在剛才大家的對話過程中已經提到了很多核心問題,希望能把這些核心問題展開,也可以針對具體作品,探討在真與美之間、說明性和詩性之間,如何去把握和控制,進一步把“遺產攝影”的框架建立起來。
史蒂文:我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所提供的這些圖片,具有很多方面的功能,一些是為了那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而特別去拍攝的,另一些是基于它的教學、教育功能,另外還有是為建筑師、建筑提供一些思路,或是推廣促進這種文化的。
現場聽眾:剛才展示的這些照片里邊,很多是展現那種透視感或者是西方現代文明的藝術,而這種視覺藝術在我們中國是,我覺得不是很能表現出來,想問一下,史蒂文先生是怎么培養這種視覺藝術風格的?
史蒂文:我去到每一處景觀拍攝的時候,我總是想用一種全新的角度去拍攝它。還有就是拍攝前要為它做研究。
黛安娜:史蒂文就是強調要先研究,要有一個全面準確的準備,然后去拍它。
現場聽眾:您好!我想問一下,遺產應該是一個有時間沉淀,有歷史價值的東西,而拍攝世界遺產的時間都比較短,那怎么用短時間的拍攝來體現一個長時間的有價值的遺產?
史蒂文:您的提問非常好,這也是我們一直要去解決的問題。作為一名攝影師,如何在很短的時間內去表現這種具有歷史厚重感的場景和某種文化的代表,這是我們一直在思考的問題。現在沒有答案,沒有結論,一切都在不斷地嘗試和努力中。
現場聽眾:想請史蒂文先生介紹一下他們團隊的工作經驗。
史蒂文:去一個地方拍攝,攝影師在那里通常只會停留三天,加上一些地理原因,天氣、環境條件等影響,時間非常有限,有的時候攝影師必須作出一種妥協。
黛安娜:世界遺產有文化遺產,還有自然遺產。拍攝自然遺產,三天時間是不夠的,因此,在自然遺產所在地,史蒂文他們有時候就培訓當地人,讓他們去拍照。被培訓的人里面既有攝影師,也有當地的遺產保護工作人員。
史蒂文:大家也知道,目前有960多處世界文化遺產,涉及到100多個國家,有時候他們不得不拍得快一點,這是一個很現實的挑戰。
現場聽眾:您好!我是北京電影學院的研究生。我覺得每組作品都會有很多的主觀情緒,甚至是一些個人想法在里邊。我想問,做展覽的時候,你們這個團隊會依據一個什么樣的原則來選取這些照片?是選擇最紀實的方法拍攝的照片,還是選擇更具有表現性的作品?
史蒂文:其實每一張照片嚴格來說都是主觀性的。因為對于藝術來說,只要你看到的都是具有主觀性的,沒有客觀性的存在,因為是你看到的,這本身就是一種主觀。但是你要去控制自己的這個主觀情緒,因為你要清楚,你是為誰服務的,你做這件事的目的是什么。雖然他都是有主觀性的,但是你不能讓自己的主觀性超越了你本身要做這件事情的目的,比如說攝影師是為誰服務的,他的客戶是誰,這個要很清楚。所以這也是一項平衡的藝術。我們選照片也就是要這樣平衡后的結果。
現場聽眾:您在拍攝這么多文化遺產的時候,包括你們的團隊,是不是需要大量地了解這個文化遺產的背景資料?
史蒂文:是的,在去每一處遺產拍攝之前,一定要做很多的研究,一定要了解當地人或者聯合國為什么認為它是重要的。攝影師研究的時候,包括要考察那個地方的建筑、人文、動物、景觀、風景一系列所有相關的內容,因為它代表了全球人類共同的財富,所以考察范圍非常廣,要進行全面的考察。
李少白:剛才欣賞了史蒂文先生關于世界遺產的作品以及聽了他的講解,我對這個世界遺產的拍攝也有自己的一些看法、想法和經驗。
我個人認為,對世界文化遺產的拍攝有各種不同方式。有進行研究式的拍攝,這就要求盡可能地利用攝影的復制功能,越準確越好,越全面越好,越細致越好;有是為宣傳用的拍攝,比如旅游畫冊等等,那么就是要拍它最典型的、最具標志性的,最好看的;還有著重于藝術性的拍攝,剛才李樹峰所長也談到了,作為這種攝影,實際上是一個視覺記憶。
我覺得,攝影面對世界遺產,不僅是強調視覺的記憶,而且也可以說是視覺的幻夢。因為有些人拍這個世界遺產,包括我在內,并不進行過多的研究,就跟我拍太陽、拍月亮一樣,我并不進行對太陽、對月亮的科學研究,我只是利用這個載體來釋放它所蘊含的或者隱藏的美或者詩意。所以我覺得,如果你對拍世界遺產感興趣,首先要弄清楚世界遺產是怎么吸引你的,你想通過拍世界遺產做什么。就是剛才史蒂文先生講了一個拍攝的原因,我覺得很有道理。客戶要求是什么,你就要按他那個拍。同時,如果你有自己的一些主觀看法,那么在很大程度上你就需要考慮到客戶的要求。
剛才大家問到,拍攝這么多照片,如果要辦展覽怎么挑選照片。我想他剛才也回答了,就是說要平衡:一個要顯示他們的這個攝影團隊的水平,另一個也不能脫離對世界文化遺產的表現。
史蒂文:有的時候對于攝影家的一種挑戰是,像路燈、天線、衛星,可能會影響到他想拍攝的主題,但是在作品中可以專門運用路燈、天線,或者是人物來呈現這一地域特點。所以對于一名優秀的攝影家來說,有的時候是需要作出一種妥協的,就是通過技術手段把一些不利的因素變為有利的因素。
楊樹田:在我看來,在拍攝世界遺產專題的時候,首先你得先了解它,然后再去對它拍攝。比如李少白老師拍故宮,他不是一次去拍攝,是多次去拍攝,在拍攝的過程中,認識都在逐漸的提高,進一步挖掘故宮的精髓部分。這是我多年來拍攝世界遺產的一個經驗。
他們拍攝的主題是“我們的家園”,緊扣這個主題,拍攝的世界遺產內容中都有很多人物的參與。這個與我們中國攝影人平常拍攝有一些不同。史蒂文先生拍的韓國建筑,就是拍它的圖案。我們的拍攝呢,首先要大景觀,介紹這個景物是怎么回事,它們的建筑結構是什么樣,結構里面的這些精華是什么。比如拍這個山西的鎮國寺,鎮國寺的建筑結構它有什么特點,你得展現出來;它內部的唐代雕像需要展現出來;然后再發現它什么呢?你得逐漸的發現,去了解,鎮國寺的每一次翻修都在梁上留下記錄,是什么時代修的,每一個捐助翻修的老百姓名字也都寫在了上面。那么,我們在拍攝它的時候要掌握的是什么?首先是它的外在結構,另外還要體現它內部的沉淀歷史,必須把它展現出來。雖然這個可能存在東西方文化的差異,但我看來,在對于世界遺產這個主題的拍攝上,初衷應該是一致的,表現手法應該是一致的。
再有,史蒂文先生拍的倫敦大本鐘,它采用慢門,將汽車通過時劃過的光影保留了下來。若換作我們,肯定是規規矩矩的拍攝,將后面的大本鐘清晰地記錄下來。我們必須要真真切切的把遺產再現出來,然后再表現光影的變化。所以我覺得,最主要的是要突出它的主題,你得讓人看清楚這個遺產是什么,不能完全都是光影,局部結構是需要的,但也不能完全都是它的局部結構,比如展覽,我需要故宮的圖片,應該是最經典、最能體現故宮的作品,不管是全貌也好,是具體局部也好,都應該拿出故宮最精華的部分來。
史民峰:剛才李樹峰老師也談到“遺產攝影”這樣一個提法,我覺得這是非常有建設性的。大家一直都在討論一個東西,就是攝影立場,我覺得,剛才從史蒂文先生最后的這種講解,包括大家不同的回答,可能都有一個解讀。
我個人覺得,“遺產攝影”既然是拍文化遺產,它有可能更重要的是文化。史蒂文先生對于文化有他的理解,我們真正去拍文化遺產,可能更重要的是對于這種文化精髓或者它背后的這種精神的解讀。目前,我們基本上都是在紀實性和藝術性之間取得一個平衡。那么,當在理解了其背后精神的同時,我們可不可以在手法上進行突破?如果在形式上或者藝術上進行突破之后,它還是不是“遺產攝影”?希望大家能進一步研究這樣一個問題。
唐東平:我特別想知道的,就是我們世界文化遺產它的整體的那個拍攝的原則,就是跟其他的風景攝影、普通的藝術攝影的區別點,它的大的框架結構到底是怎樣的?今天聽下來以后,我們大體也知道了一些輪廓。接下來就是我們要做更細致的研究。剛才譚明老師說的非常好,就是我們國內的很多攝影師非常優秀,李少白老師拍了有20多年文化遺產,李建惠老師拍頤和園也拍了10多年了。我們是慢慢的漸入佳境,是有一個積淀和發現,再發現,最后達到日臻完善的一個過程。如果三天之內我們就搞定的話,我們中國攝影家可能就是對這個還持不認可的態度。但作為一個團隊操作,作為一個公司行為、企業行為這么去做,我們是可以理解的。因為這么大的一個項目,它必須得講究效率,必須根據它的經費和人員情況去實施。這與自由攝影師,用一輩子時間去拍故宮,用一輩子時間去拍長城,用一輩子時間去拍頤和園不一樣。由此,我有一個想法,如果我們把這些長期從事拍攝遺產的攝影家進行統計,把他們拍的東西定期或者不定期的進行整理和編撰,這樣的話,對人類文明能夠起到一個真正的推動作用。
另外,我們需要有精品意識。如今,大家的眼光都已經全球化,見到了很多很多精細的、非常優秀的作品,所以對于那些粗糙的,不太注重細節,或者很隨意的照片已經不認可了。史蒂文先生剛剛展示的一些作品理念很好,但欣賞之后總有美中不足的感覺,但這情有可原,是可以理解和接受的。史蒂文先生一直在強調有時候不得不妥協,我也很欣賞他的這種“妥協”的精神。同時,對于那些不妥協的人,那些追求完美,講究完美主義的人,我覺得還是要給他們更多的空間。
金寧:聽一上午受了很多啟發。“遺產”是一個非常復雜的概念,而且很龐雜。在我看起來,不同的人看遺產會有不同的感受。事實上,我們在遺產前有時候會冠以“文明”或者“文化”這種概念。但是如果我們從情感的角度來講的話,其實有很多遺產從歷史的存留,從它當時的出發點來說,可能恰恰是反文明和反文化的。遺產真的很復雜。何為世界遺產?我想大概國際上有一個標準,這個我們就不多談了。但是“遺產”在其所在地的人們心中的位置和情感究竟如何,我想只有此時此地的本土攝影家才有這種感觸。就是說,評定一個遺產的標準,它是否符合人類共同的遺產標準,得有一個相關的機構去制定它,但是它在人們心中到底處在一個什么位置,我們如何去體驗它,去感受它,它今天在我們的生活中到底是處在一個可有可無的位置,還是一個很重要的位置。我想這個真的是只有我們本鄉本土的人才有這種更深切的體會。我很懷疑我們做遺產拍攝是保持一種所謂中立的態度,我覺得無論是價值中立,還是情感中立,這幾乎是做不到的。可能我更愿意去想,如果有這樣一種可能,應該是作為遺產的這種拍攝,它和遺產本身共同呈現一種見證的作用的話,我倒是很愿意更多的去看本鄉本土的攝影家的這種拍攝。這種再現所蘊含的影像呈現本身不完全是一個技術問題,它包含了我們和它共處在同一個空間下,我們的切身感受和對文化的體悟。在這個意義上來說,我覺得所有的選擇都是主觀的,同時所有的選擇也都連帶著我們作為一個民族共同體的一種記憶在里面,這是一個不能忽視的問題。